李安之所以成为李安,电影路上经历了什么?
李安出生于台湾,在纽约大学求学,并在实战中逐渐成熟。他用《断背山》和《卧虎藏龙》等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打破了文化之间的界限。不过,李安也有件事情绝对不会做:那就是重复自己。如此就更可以理解“比利雷恩”的120帧。
撰稿:格伦·肯尼
“今天是个做采访的好日子。”一个安静的早晨,李安在曼哈顿中城这么说。在着手进行最新的电影冒险之前,这位导演正处在短暂的平静期之中,要从一个办公室赶往另一个办公室。尽管我们见面的地方比较空旷,李安也很低调安静,但是他那种谦谦之风却似乎让整片空间都变得充实起来。
李安的作品是一个悖论。尽管他行事温和,但在艺术上向来极为大胆。他在各种形式之间来回穿梭,并且勇于承担风险。在争议纷纷的《绿巨人》中,他试图赋予漫画书式的英雄以人类的真情实感。在《色戒》中,色情惊悚片的特质被用来描述更深层次,更深刻的东西。至于他的最新故事片《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则是一部描写60年代反文化思潮剧变的成长叙事片,这听起来并不特别颠覆,除非当你考虑到它不仅是部成长叙事片,还是部同性恋出柜片。
李安出生在台湾,曾执导过题材各异、令人印象深刻的数部人文主义影片,包括《喜宴》,《饮食男女》,《冰风暴》,《与魔鬼共骑》等。他因改编了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而被提名美国导演工会奖(DGA Award),又因《卧虎藏龙》和《断背山》而赢得了美国导演工会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当听李安讲述自己的工作方法时,你会被他理念中的悲悯所折服。他说非常荣幸能够接受美国导演公会的专访,并且会把这种场合当成一次详述自己艺术准则的机会,不仅仅是为了工会的成员们,也是为了他自己。“可以有地方与我的同行们分享建议和经验,这样很不错,”他说。
怎么走上导演之路: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既是一个台湾电影人,也是一个美国电影人,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你是怎么开始,又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吧。
李安:我是在台湾长大,在非常没有艺术氛围的环境下成长的。我的家庭,还有我所处的文化都告诉我们要去学习一些实用的东西,考进一所好大学,然后来美国学习,得到学位。但是,因为太紧张,我在大学入学考试时考砸了。后来我进入台湾艺术大学(当时的国立台湾艺专),主修戏剧和电影。在七十年代初期,台湾是没有什么戏剧可以做的。而一旦我站上舞台,作为一个演员,我就深深的爱上了戏剧。我在学校过得非常开心,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多西方戏剧。我开始观看许多影片,比如伯格曼、雷诺阿这样大师的电影。23岁时,我进入伊利诺伊大学,主修戏剧。我在这所大学呆了两年,这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开始如饥似渴的接触西方文化,文学,科学或社会科学接触的不多,戏剧倒是最多的。

李安:我是在美国学习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当时英语很糟糕,只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正因如此,我没办法当演员,就从演员转行成了导演。可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吸收了很多可以改变我的东西。我在农业文化中长大,它试图强调和平与社会和自然的平衡,所以会努力尽可能减少冲突。但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戏剧文化中,一切都是冲突,它主张个人自由意志,还有个人意志如何在家庭内甚至更大的社会内创造冲突。我发现自己对于处理这种情况比较有天分。最后,在我接触了电影,每个周末都要看上五到七部电影之后,我发现我是想拍电影的。我在纽约大学上了研究生,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电影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计划,你只需要走出校门去拍电影就好了。
记者:那么你是怎么从学生变成专业人士的?
李安:嗯,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有整整六年都发展得非常糟糕。在纽约大学我们拍摄短片,我还因为短片在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得到了一个经纪人。但实际情况是,从学校毕业以后,我花了三年才理解短片和叙事片之间的区别。没有人真正教过我们如何去拍叙事片长度的结构,它又是怎么样运作,怎么样来培养角色。所以后来我又迷失了。我在好莱坞试图推销自己,不过项目一个接一个全部失败。可是,经过那些年月,我教会了自己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件是,叙事片长度的剧本应该如何运转,还有这个市场需要什么。
记者:后来你是如何突破的?
李安:1990年,我参加了一个台湾政府举办的剧本比赛。奖金很丰厚。一等奖有16000美元,二等奖有8000美元。我同时赢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一等奖是《推手》。这是我专门为这个比赛而写的剧本,二等奖是《喜宴》,这是我五年前写的,获得了二等奖,也成了我的第二部电影。我写的《喜宴》在美国太中国化了,在台湾又太同性恋了。所以我一直都没什么行动。我便把两个剧本都送去,并双双获奖。《推手》是关于一个台湾家庭在纽约的一个小故事,然后一家台湾的工作室就想投资拍摄《推手》。他们给了我40万美元,让我在纽约拍片。我被引荐给了Good Machine,一家特德·霍普和詹姆斯·沙姆斯共同创办的公司。我向他们推销我的故事。詹姆斯对我说,“难怪你整整六年一事无成,你是最糟糕的推销员。你的推销总是不得要领。”他们向我推销自己,号称自己是无成本电影制作之王。不是低成本,而是无成本!因此我们联合起来做了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台湾反响很好,也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上映,因为这部片子很卖座,所以台湾的工作室给了我更多钱。它给了我75万来拍摄《喜宴》。詹姆斯说,“让我来帮你修改剧本。”他这么做了,剩下的,我想说,就是历史的力量了。
记者:从这儿开始就奠定了你和沙姆斯的长期合作。自从1993年以来,你们共同撰写并且创作了近十部影片,而且作为焦点电影公司的总裁,他也替你发行了几部影片,你们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帮助你稳定地产出电影的呢?
李安:这是一个非常有机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成绩是由我们的友谊产出的,而不是因为任何伟大的计划。当时《喜宴》被《理智与情感》未来的制片人看到了,因为这部影片,他觉得我很适合改编简·奥斯汀的作品。我去找詹姆斯帮忙并且问他我应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考虑和对方合作英文电影了。但是正好制片人带着《理智》一片来问我的意见,我没法决定是要拍还是不拍。一个原因是预算足足有一千六百万美元,我从没管过这么多的钱,再说我也从没拍过剧情片。可我又没有办法拒绝与艾玛·汤普森合作的诱惑,我读了艾玛·汤普森写的剧本,尽管我的英文那个时候不是太流利,但我从心里感觉到,这部片子和我想做的东西是很相似的。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去了英国。我当时很害怕。我的英语很蹩脚,可我要拍的是简·奥斯汀。我有一个顶级的英语演员团队和剧组,他们来自牛津大学和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这是最棒的演员和剧团,我当然会觉得很害怕了,于是我带了詹姆斯跟我一同前行。在那时候,还有拍摄期间我们都在一块。詹姆斯就像是我的发言人。他会与这些人进行社交,而我则做好自己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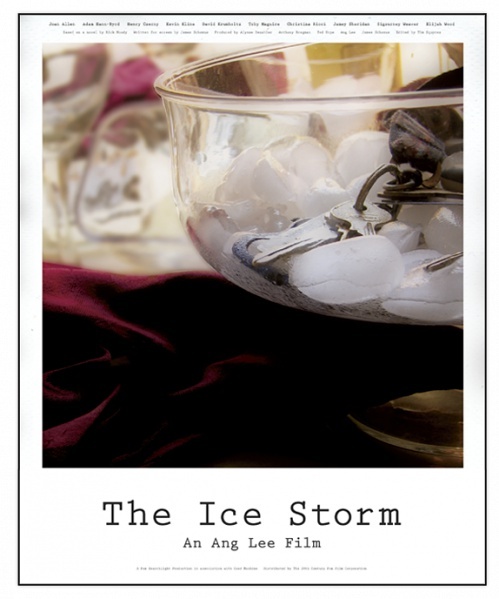
李安:我读到这本书是因为詹姆斯的推荐,本来我并不觉得一定要把它拍成电影,可等我读到米奇·卡弗滑下冰雪这个片段时,这个影像就出现在我脑海里了。我告诉詹姆斯,“我想把它拍成一部电影。”他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我们就去见了这本书的作者里克·穆迪,基本上没花多少钱就买到了改编权。《理智与情感》打断了这个过程,不过后来我们回头去做了这部片子。这也是詹姆斯个人为我写的第一部剧本。
问:在这个国家用《冰风暴》有所成就后,你再回到中国拍摄《卧虎藏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答:我既用英语,也用汉语导演,并且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对我来说,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平衡。在美国电影中,因为美国文化是一种被改变过的文化,所以技能和艺术创作变得更加清晰。在某些方面,在心理上来说也更容易。我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潜台词。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会看到的第一件事是文字的准确性,但是,理解文化习惯才是更加困难的。然后,一旦我已用英语导演,又回归到汉语,开始拍摄《卧虎藏龙》后,我发现我的思维已经西化,全球化了很多。所以我必须找到我的方式,好回到中国文化,我的第一个文化之中。

记者:在职业生涯中,你已经拍过了内战的故事,改编过超级英雄故事,还有现代西方的故事。你认为自己从一个形式再转到另外一个形式的原因是什么?
李安:我有这种恐惧,如果我一直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就无法带来那种我想要的新鲜感了。如果一直执着于拍摄一种形式,我很担心自己会变得更加不诚实,因为在某种特定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熟练性可能会让我,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可以伪造出这种片子。为了把工作做到最好,我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会让我还不太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它必须让我感觉到我好像还是在拍摄第一部电影。如果我觉得自己是在重复什么事情,或者是重复我自己,我会觉得非常害怕,甚至比接受新挑战还要害怕。
记者:这就是你定期更换摄影师的原因?
李安:我觉得连续几部片子都跟某个人合作应该是很有意思的,这种关系会日益加深,并在艺术上带来丰厚回报。关于摄影师,我个人有几条坚持的原则。要是我跟他们合作,一定是出于特定的原因。拍《冰风暴》时我找了弗雷德里克·埃尔姆斯,因为那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电源没了,灯光也熄灭了。我需要摄影师让我们有种错觉,就是观众可以看到人们在黑暗中的行动。这是戏剧性的核心。我太佩服弗雷德,尤其是在他与大卫·林奇在《蓝丝绒》里的表现了。弗雷德把曝光降低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最低指数,拍出了这些精彩的、实验性的东西。
对于视觉效果处理:
记者:对《断背山》你是怎么处理视觉效果的?
李安:我去找了罗德里戈·普列托,《爱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 Babel)的摄影来拍《断背山》,因为我认为他技术很不错,也希望可以尽快拍摄完成。但后来我让他拍摄那种相反的,他擅长的风格,他便能够给出《断背山》我想要的那种安静,几乎是被动的样子。我对有才华的人的才华很有信心。
记者:你如何与摄影师合作?
李安:我喜欢与有两种与众不同态度的摄影师合作,不论年龄或经验。首先,我想要他们跟我讨论戏剧本身,而不是视觉效果。我不担心如何拍摄它。如果我们专注于帮助演员塑造角色,并且让他们能够自在的演戏,该来的自然会来。我希望摄影师能对讲述故事内容感兴趣。这是我的头号准则。其次我不希望任何人表现得他或她是个无所不知的高手。我想和那些觉得自己还在学习的人合作,他们不会自动拥有所有的答案。当我遇到人,询问他们对什么东西的看法而他们答不上来时,我就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李安:嗯,你知道,钢丝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特殊效果,它没有办法脱离人存在。在《卧虎藏龙》的竹林对战里,我们有数十人在地面上实际操作各种元素。角色的人性和性格跟他们飞翔的方式都有关系,这是在写作中没有指明,但是在拍摄中被设想并实施的。举例来说,章子怡的角色看起来能自由地飞翔,而杨紫琼饰演的角色则跑得非常快,她飞快奔跑获得的能量让她能够向上飞跃。这些特殊的技术对于表现角色很有用。
记者:这在《绿巨人》上有什么不同?
李安:对于《绿巨人》,我是用一种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我想象着自己在使用一种非常崭新,非常昂贵的工具。它在商业上面很有问题,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部恐怖影片而不是一部漫画改编影片,而且得把它像《蜘蛛侠》一样推销出去,对我来说这个主题是和“卧虎”一脉相承的。在那部影片中,“藏龙”意指文化中内含却被压抑的东西——在东方是性爱,在《绿巨人》的美国则是愤怒和暴力。结果我们发现,如果我自己穿上动作捕捉服,让他们来拍摄我的面部表情,要比我自己向那些动画人员做出描述要好的多,可以让他们少工作上数周。后来我亲自表演了绿巨人的动作,并且表现出了他的愤怒,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喜欢和CG合成动画以一种观众无法看到的方式合作。我们其实在《断背山》上也用了一些CG动画来做风景,如果你想让一朵云在停留在画面的某个地方,你就可以这么做。它非常好用。
记者:《冰风暴》中的一些特定影像是否让你遗憾在拍摄时还没有今天的特效工具?
李安:没有,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们观看电影时,一般电影的平均长度是1小时40分钟或者2小时。我相信,人们真正专注的时间大概只有十或者十五分钟。拍电影就是拍人。没有东西可以比人脸更加吸引观众注意力,因为观众会认得这些面孔。讲故事,戏剧和人类的面孔——这就是我想要完成的重心事情。我花了一部又一部电影试图超越它,来创造更多的视觉效果,因为我喜欢差异性。但是,你只能做这么多。电影必须是属于角色的。
记者:在所有的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是恩尼斯在片尾拜访杰克的父母那一幕。你怎么去设置那种情绪呢?
李安:嗯,这是一踏上拍摄现场我们就会考虑到的。那是我在电影里最喜欢的一幕。这是一个非常坚忍的场景,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不在的人的场景。杰克·吉伦哈尔很生动地演出了这一幕,关于这个所有人都失去了的人的一幕。我的视觉灵感来自安德鲁·怀斯,还有丹麦画家威尔海姆·哈姆休伊的那些光秃秃的,白色的门。因此,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合适的房子,合适的空间,当然,这是我的美工设计师朱迪·贝克尔的任务。为了拍摄那一幕,我使用了曾经在《绿巨人》中用过的风格。我用两架摄像机拍摄,从两侧拍摄演员,然后更换镜头,并且再拍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方式。当你在一起编辑时,你可以对某些反应,情绪有一定强调。这样拍摄可能会让一些演员摸不着头脑。但是希思·莱杰,彼得·迈克罗比和罗伯塔·马克斯韦尔都没有,这让我很喜欢。那一天很奇怪。我正想着需要一些阳光,阳光就来了,我还记得自己走向现场,觉得今天会是很棒的一天。这样的场景,演员和他们的面孔让这一切完美起来。
怎么与演员的合作:

李安:这事情我可以说很久很久,因为每个演员都是不同的,每个演员都像是一座你必须爬过的山。当然,没有任何事情是容易的。我认为某个人全神贯注投入非常多的精力来制作电影时,这些主角会成为导演的重要部分,所以你会把自己和演员融入到一起,并且演员们也知道这一点。你在看着他们,他们也在看着你。而且我也会思索,要怎么样才能把他们变成我心目中的那个人?他们也在看着我,试图找出我想要什么,这样他们才可以演得出来。我说过我跟摄影师,美工设计师,作家和制片人的关系,我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了他们。但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把自己最好的部分给了演员。这并不代表我是演员的朋友,实际上我基本不跟他们来往。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冷酷。但是我只干自己认为有必要的事情。我只是为了把我想要的东西和艺术的时刻表达出来,并且让它们永远凝固在赛璐珞上。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非常不简单,制作电影对我来说是相当神圣的事情。我觉得演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记者:让新人和老将同场飙演技有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李安:让他们同时出演肯定会出现很多困难,我拍摄《理智与情感》时,凯特·温斯莱特只有19岁,这是她的第二部电影,所以有些事情对她就会比较困难,比如说应付摄像机,还不能意识到它。当然她现在已经可以掌控这一切了,只是那时她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大好。但是对于艾玛·汤普森来说,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艾玛的演技是很纯熟的。她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次就表达四五层的情感。但是,尽管凯特相对还比较稚嫩,她却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可以让观众不自觉地为她担忧。这对凯特来说很简单,但是对艾玛来说就比较难了。在这部片中她们出演姐妹。
记者:当你要和演员们开始合作时,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李安:首先,你必须让自己意识到演员的呼吸和感觉。排练有助于让你进入这一状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拍摄的时候。通常我会做两三个星期的排练。这个排练并不是要像真正拍电影一样。我认为电影演员不会在排练时倾尽全力,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排练时就倾尽全力,在正式拍摄时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么做了。如果他们在排练时有所保留,那么你真正想要的那些品质就会保留到正式拍摄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排练就是要帮助我们来看清演员。而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要亲自看到角色在演员之中成形的过程,演员是如何培养这个角色的味道而且让角色与其他人发生化学反应。到了现场,我们都必须和摄影机打交道,而且都会拍摄当下,你必须去思考和感受。因此排练时候的效果并不是真正演出的效果,而只是一种共同思考的方式。
怎么对待“导演”这一职业:


李安:我认为电影是一种人工介质。它不是生活。它不是真实。但它肯定有着自己的生命。有着你必须膜拜的电影之神。有时候你必须放弃每个人的意见,只听电影之神的声音。我会首先去做很多事情,但后来我就有点像是成了观察者,并且会决定应该走哪条路来符合电影之神的意图。我认为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道路,我告诉我的演员和剧组成员,这无关我们,也无关我自己。我们都是电影的俘虏。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试着来调整大家,带来团结。
记者:你来到现场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李安:我在拍电影时会在早上做好计划,然后演员们回来化妆,我给出分镜头表。我会与助理导演,摄像以及美工部门一起协商接下来的场景。我们准备好场景之后,就会继续探讨细节并且将它们逐步改进。再接下来就是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直到你确定想要哪一幕。
记者:一个镜头要拍几次?
李安:大概要拍六到七次,一般来说,很难超过十二次,但是也不会少于三次。拍《色戒》时,只要超过五次,汤唯就会变得注意力涣散。她非常情绪化,非常容易波动,因为她是第一次拍电影嘛。她会在现场立马融入情绪,然后就走神了。对于其他经验比较少的演员来讲就大不一样。比如说《色戒》里面的王力宏,或《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德米特里·马丁都是新人电影演员,他们的表现会一次比一次好。有时候他们的第七次就会比第六次好。但在同一个镜头里,也有可能直拍到第五次都不如意。不过,也会有理想的演员。比如说,《色戒》里的梁朝伟或《冰风暴》的琼·艾伦,不管拍上多少次他们的表现都是很完美的。所以各种情况都会有。有很多混合,配合以及平衡要做。
记者:在《色戒》里你把极度浓烈的感情与非常露骨的性爱场面相结合,这样是不是很难达到合适的平衡呢?
李安:是的。这两个角色都试图杀死对方。他是逼供者,她是诱奸者,我找不到比这更加浓烈的感情了。我会和演员们说到与妻子家人都不会接触到的题材,因为我与演员们分享最为私密的空间,对他们也都非常直接。我们就是从这些材料之中创造出自己的艺术并且在那个层面上有所连结。我是在用这些角色来暴露我自己。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经历。至于性爱场面,我认为我们是在突破表演的某些界限。你必须监督表演,并且创建一个境遇,让你反思在你面前发生的所有一切是否真实。那就是一个导演能与演员们享有的最终极的体验。但那也是非常可怕的。这部片拍完以后我们都有一个月很不舒服。它就是有那么激烈。拍完这部影片之后,生平第一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演员们从这部片子里拉回来。我还和汤唯有着联系,帮她从那个角色里解脱。而在过去,我并不认为这是我自己的工作。
记者:你跟演员们通常维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李安:我不知道演员对我的感觉如何。当我第一次执导英语电影还摒弃了蛮多东西的。因为我的英语讲得很不好,所以会给出非常直接了当的指示。一开始演员们都很震惊,到后来他们懂得这是因为我的英文说的很烂,也不知道怎么把英文说得更好,所以都容忍了我。但是后来我的英文越说越好,也就有所收敛,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变得更加文明。我在拍《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开始有所放松,有点是因为拍摄《色戒》时感情过于浓烈了。抛开想让题材更加正面向上不说,我个人决定要变得更加温和友善,而且确保大家都更加开心。
面对“电影市场”拍片有什么计划:

图为《少年P的奇幻漂流》工作照
记者:你的一些影片似乎是为国际观众量身打造的,但是在海外他们的市场如何呢,尤其是在亚洲市场?
李安:我们在亚洲市场的经历相当有趣。拍摄《卧虎藏龙》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拍武打片。但同时我又想拍摄更高级的武打片。我并不想拍摄童年看的那种香港B级武打片。后来我们就把这部片子拍成了A级片与B级片的结合。这种做法在东方市场并不是很受欢迎,虽然我们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新方法在这里更受到欣赏。但是《色戒》的反响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东方它造成了一种巨大的文化现象,但是在西方它却并没有收到什么反响。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西方观众跟那段历史没有直接联系,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东方观众更加能够接受它的悲剧性,而不是西方观众。
记者:中国的观众又是什么样的呢?
李安:中国内地电影现在才要真正开始起飞。这是一个新的市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市场。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制造自己的中庸式的电影。虽然盗版侵权无处不在,但是观众们仍然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你可以看看在中国大热的片子,就算是我,也很难了解为什么中国观众会喜欢这些东西,为什么又不喜欢某些东西。中国观众的人数是美国观众的四倍,也就是说,就算某部影片只在一个城市放映,也可能会回收上亿的票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记者:鉴于市场的复杂性,你觉得你拍摄的这些影片还会有市场空间吗?
李安:我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区域。我拍的电影可以说是大型的小电影,并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而且我会去拍那些自己想拍的影片。在国际影界方面,我认为在美国以外有很多有趣的电影。而且美国的艺术工作室出品的影片常常被定位为低成本影片。除了这个我们还有好莱坞电影。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很多可以被称为“墙头草”的电影。现在的电影是两极分化非常厉害的。有很多艺术成就已经非常高的导演们会得到更多的钱来拍摄更多影片,但并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这样。
记者:你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根据扬·马特尔的书改编的。它讲述了一个少年与一头斑马,一只鬣狗,一只猩猩和一只老虎被困在救生艇上,在太平洋漂流的冒险故事。这听起来似乎很棘手,而且似乎需要许多准备工作。
李安:2001年我初读这本书时就被迷住了,但那时我并不认为它可以被拍成电影。后来我开始拍摄《创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福克斯2000来找我并且说,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可以启动了。我认为这部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层面的难度。它包含了动画,所以视觉预览将开始发挥作用。我不喜欢视觉预览,通常也不做故事板。有时我做,但不会全部按照故事板来。为什么你要跟着故事板来拍镜头,而不是去尝试找到某些东西,并且利用它来为你的影片服务呢?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导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拍摄昂贵的镜头时,你必须做一个详细的计划。你不敢随便采用平常的计划,怕输不起。这十分令人兴奋,这就是电影制作,电影制作之中从来不讲规则。
探究《盗梦空间》《蝙蝠侠》系列导演诺兰的电影世界
奇异旅程——《魔戒》导演彼特-杰克逊谈在电影之路上走得多远
专访马丁·斯科塞斯,解读电影最不可缺少的元素
专访斯皮尔伯格:怎么讲一个“成功”的故事?
专访《异形》导演雷德利·斯科特
专访《泰坦尼克号》《阿凡达》导演卡梅隆
DGA专访老爷子伊斯特伍德
专访《楚门世界》《死亡诗社》导演彼得·威尔
更多电影人专访/院线片“观感度解析”请见:观影频道
撰稿:格伦·肯尼
翻译:吴晓辉 如需转载,请标注来源影视工业网,感谢!
原文地址:http://www.dga.org
——————————————————————————————————————————

原文地址:http://www.dga.org
——————————————————————————————————————————
跨越国界

李安的作品是一个悖论。尽管他行事温和,但在艺术上向来极为大胆。他在各种形式之间来回穿梭,并且勇于承担风险。在争议纷纷的《绿巨人》中,他试图赋予漫画书式的英雄以人类的真情实感。在《色戒》中,色情惊悚片的特质被用来描述更深层次,更深刻的东西。至于他的最新故事片《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则是一部描写60年代反文化思潮剧变的成长叙事片,这听起来并不特别颠覆,除非当你考虑到它不仅是部成长叙事片,还是部同性恋出柜片。
李安出生在台湾,曾执导过题材各异、令人印象深刻的数部人文主义影片,包括《喜宴》,《饮食男女》,《冰风暴》,《与魔鬼共骑》等。他因改编了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而被提名美国导演工会奖(DGA Award),又因《卧虎藏龙》和《断背山》而赢得了美国导演工会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当听李安讲述自己的工作方法时,你会被他理念中的悲悯所折服。他说非常荣幸能够接受美国导演公会的专访,并且会把这种场合当成一次详述自己艺术准则的机会,不仅仅是为了工会的成员们,也是为了他自己。“可以有地方与我的同行们分享建议和经验,这样很不错,”他说。
怎么走上导演之路: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既是一个台湾电影人,也是一个美国电影人,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你是怎么开始,又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吧。
李安:我是在台湾长大,在非常没有艺术氛围的环境下成长的。我的家庭,还有我所处的文化都告诉我们要去学习一些实用的东西,考进一所好大学,然后来美国学习,得到学位。但是,因为太紧张,我在大学入学考试时考砸了。后来我进入台湾艺术大学(当时的国立台湾艺专),主修戏剧和电影。在七十年代初期,台湾是没有什么戏剧可以做的。而一旦我站上舞台,作为一个演员,我就深深的爱上了戏剧。我在学校过得非常开心,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多西方戏剧。我开始观看许多影片,比如伯格曼、雷诺阿这样大师的电影。23岁时,我进入伊利诺伊大学,主修戏剧。我在这所大学呆了两年,这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开始如饥似渴的接触西方文化,文学,科学或社会科学接触的不多,戏剧倒是最多的。

李安在《理智与情感》片场
记者: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对导演比对演戏更感兴趣?李安:我是在美国学习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当时英语很糟糕,只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正因如此,我没办法当演员,就从演员转行成了导演。可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吸收了很多可以改变我的东西。我在农业文化中长大,它试图强调和平与社会和自然的平衡,所以会努力尽可能减少冲突。但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戏剧文化中,一切都是冲突,它主张个人自由意志,还有个人意志如何在家庭内甚至更大的社会内创造冲突。我发现自己对于处理这种情况比较有天分。最后,在我接触了电影,每个周末都要看上五到七部电影之后,我发现我是想拍电影的。我在纽约大学上了研究生,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电影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计划,你只需要走出校门去拍电影就好了。
记者:那么你是怎么从学生变成专业人士的?
李安:嗯,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有整整六年都发展得非常糟糕。在纽约大学我们拍摄短片,我还因为短片在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得到了一个经纪人。但实际情况是,从学校毕业以后,我花了三年才理解短片和叙事片之间的区别。没有人真正教过我们如何去拍叙事片长度的结构,它又是怎么样运作,怎么样来培养角色。所以后来我又迷失了。我在好莱坞试图推销自己,不过项目一个接一个全部失败。可是,经过那些年月,我教会了自己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件是,叙事片长度的剧本应该如何运转,还有这个市场需要什么。
记者:后来你是如何突破的?
李安:1990年,我参加了一个台湾政府举办的剧本比赛。奖金很丰厚。一等奖有16000美元,二等奖有8000美元。我同时赢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一等奖是《推手》。这是我专门为这个比赛而写的剧本,二等奖是《喜宴》,这是我五年前写的,获得了二等奖,也成了我的第二部电影。我写的《喜宴》在美国太中国化了,在台湾又太同性恋了。所以我一直都没什么行动。我便把两个剧本都送去,并双双获奖。《推手》是关于一个台湾家庭在纽约的一个小故事,然后一家台湾的工作室就想投资拍摄《推手》。他们给了我40万美元,让我在纽约拍片。我被引荐给了Good Machine,一家特德·霍普和詹姆斯·沙姆斯共同创办的公司。我向他们推销我的故事。詹姆斯对我说,“难怪你整整六年一事无成,你是最糟糕的推销员。你的推销总是不得要领。”他们向我推销自己,号称自己是无成本电影制作之王。不是低成本,而是无成本!因此我们联合起来做了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台湾反响很好,也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上映,因为这部片子很卖座,所以台湾的工作室给了我更多钱。它给了我75万来拍摄《喜宴》。詹姆斯说,“让我来帮你修改剧本。”他这么做了,剩下的,我想说,就是历史的力量了。
记者:从这儿开始就奠定了你和沙姆斯的长期合作。自从1993年以来,你们共同撰写并且创作了近十部影片,而且作为焦点电影公司的总裁,他也替你发行了几部影片,你们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帮助你稳定地产出电影的呢?
李安:这是一个非常有机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成绩是由我们的友谊产出的,而不是因为任何伟大的计划。当时《喜宴》被《理智与情感》未来的制片人看到了,因为这部影片,他觉得我很适合改编简·奥斯汀的作品。我去找詹姆斯帮忙并且问他我应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考虑和对方合作英文电影了。但是正好制片人带着《理智》一片来问我的意见,我没法决定是要拍还是不拍。一个原因是预算足足有一千六百万美元,我从没管过这么多的钱,再说我也从没拍过剧情片。可我又没有办法拒绝与艾玛·汤普森合作的诱惑,我读了艾玛·汤普森写的剧本,尽管我的英文那个时候不是太流利,但我从心里感觉到,这部片子和我想做的东西是很相似的。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去了英国。我当时很害怕。我的英语很蹩脚,可我要拍的是简·奥斯汀。我有一个顶级的英语演员团队和剧组,他们来自牛津大学和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这是最棒的演员和剧团,我当然会觉得很害怕了,于是我带了詹姆斯跟我一同前行。在那时候,还有拍摄期间我们都在一块。詹姆斯就像是我的发言人。他会与这些人进行社交,而我则做好自己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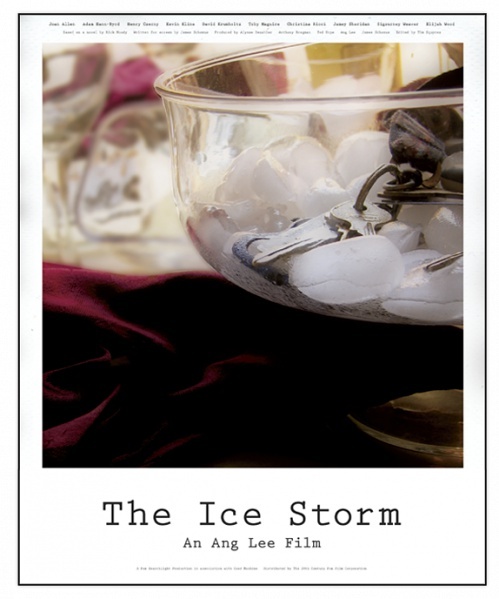
影迷自制的《冰风暴》海报
记者:继《理智与情感》后,你又拍了《冰风暴》,这部片子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美国在七十年代初期的风俗习惯。这个项目又是怎么来的呢?
怎么维持导演之路的:
李安:我读到这本书是因为詹姆斯的推荐,本来我并不觉得一定要把它拍成电影,可等我读到米奇·卡弗滑下冰雪这个片段时,这个影像就出现在我脑海里了。我告诉詹姆斯,“我想把它拍成一部电影。”他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我们就去见了这本书的作者里克·穆迪,基本上没花多少钱就买到了改编权。《理智与情感》打断了这个过程,不过后来我们回头去做了这部片子。这也是詹姆斯个人为我写的第一部剧本。
问:在这个国家用《冰风暴》有所成就后,你再回到中国拍摄《卧虎藏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答:我既用英语,也用汉语导演,并且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对我来说,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平衡。在美国电影中,因为美国文化是一种被改变过的文化,所以技能和艺术创作变得更加清晰。在某些方面,在心理上来说也更容易。我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潜台词。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会看到的第一件事是文字的准确性,但是,理解文化习惯才是更加困难的。然后,一旦我已用英语导演,又回归到汉语,开始拍摄《卧虎藏龙》后,我发现我的思维已经西化,全球化了很多。所以我必须找到我的方式,好回到中国文化,我的第一个文化之中。

图《卧虎藏龙》工作照
记者:在职业生涯中,你已经拍过了内战的故事,改编过超级英雄故事,还有现代西方的故事。你认为自己从一个形式再转到另外一个形式的原因是什么?
李安:我有这种恐惧,如果我一直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就无法带来那种我想要的新鲜感了。如果一直执着于拍摄一种形式,我很担心自己会变得更加不诚实,因为在某种特定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熟练性可能会让我,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可以伪造出这种片子。为了把工作做到最好,我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会让我还不太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它必须让我感觉到我好像还是在拍摄第一部电影。如果我觉得自己是在重复什么事情,或者是重复我自己,我会觉得非常害怕,甚至比接受新挑战还要害怕。
记者:这就是你定期更换摄影师的原因?
李安:我觉得连续几部片子都跟某个人合作应该是很有意思的,这种关系会日益加深,并在艺术上带来丰厚回报。关于摄影师,我个人有几条坚持的原则。要是我跟他们合作,一定是出于特定的原因。拍《冰风暴》时我找了弗雷德里克·埃尔姆斯,因为那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电源没了,灯光也熄灭了。我需要摄影师让我们有种错觉,就是观众可以看到人们在黑暗中的行动。这是戏剧性的核心。我太佩服弗雷德,尤其是在他与大卫·林奇在《蓝丝绒》里的表现了。弗雷德把曝光降低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最低指数,拍出了这些精彩的、实验性的东西。
对于视觉效果处理:
记者:对《断背山》你是怎么处理视觉效果的?
李安:我去找了罗德里戈·普列托,《爱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 Babel)的摄影来拍《断背山》,因为我认为他技术很不错,也希望可以尽快拍摄完成。但后来我让他拍摄那种相反的,他擅长的风格,他便能够给出《断背山》我想要的那种安静,几乎是被动的样子。我对有才华的人的才华很有信心。
记者:你如何与摄影师合作?
李安:我喜欢与有两种与众不同态度的摄影师合作,不论年龄或经验。首先,我想要他们跟我讨论戏剧本身,而不是视觉效果。我不担心如何拍摄它。如果我们专注于帮助演员塑造角色,并且让他们能够自在的演戏,该来的自然会来。我希望摄影师能对讲述故事内容感兴趣。这是我的头号准则。其次我不希望任何人表现得他或她是个无所不知的高手。我想和那些觉得自己还在学习的人合作,他们不会自动拥有所有的答案。当我遇到人,询问他们对什么东西的看法而他们答不上来时,我就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图为《卧虎藏龙》剧照
记者:在你的几部电影中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元素,比如《卧虎藏龙》,这部片子里的钢丝令人感觉到演员们在凌空飞翔,《绿巨人》则用CGI动画来还原漫画角色。你做特效工作时要如何保持角色的人性化?李安:嗯,你知道,钢丝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特殊效果,它没有办法脱离人存在。在《卧虎藏龙》的竹林对战里,我们有数十人在地面上实际操作各种元素。角色的人性和性格跟他们飞翔的方式都有关系,这是在写作中没有指明,但是在拍摄中被设想并实施的。举例来说,章子怡的角色看起来能自由地飞翔,而杨紫琼饰演的角色则跑得非常快,她飞快奔跑获得的能量让她能够向上飞跃。这些特殊的技术对于表现角色很有用。
记者:这在《绿巨人》上有什么不同?
李安:对于《绿巨人》,我是用一种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我想象着自己在使用一种非常崭新,非常昂贵的工具。它在商业上面很有问题,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部恐怖影片而不是一部漫画改编影片,而且得把它像《蜘蛛侠》一样推销出去,对我来说这个主题是和“卧虎”一脉相承的。在那部影片中,“藏龙”意指文化中内含却被压抑的东西——在东方是性爱,在《绿巨人》的美国则是愤怒和暴力。结果我们发现,如果我自己穿上动作捕捉服,让他们来拍摄我的面部表情,要比我自己向那些动画人员做出描述要好的多,可以让他们少工作上数周。后来我亲自表演了绿巨人的动作,并且表现出了他的愤怒,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喜欢和CG合成动画以一种观众无法看到的方式合作。我们其实在《断背山》上也用了一些CG动画来做风景,如果你想让一朵云在停留在画面的某个地方,你就可以这么做。它非常好用。
记者:《冰风暴》中的一些特定影像是否让你遗憾在拍摄时还没有今天的特效工具?
李安:没有,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们观看电影时,一般电影的平均长度是1小时40分钟或者2小时。我相信,人们真正专注的时间大概只有十或者十五分钟。拍电影就是拍人。没有东西可以比人脸更加吸引观众注意力,因为观众会认得这些面孔。讲故事,戏剧和人类的面孔——这就是我想要完成的重心事情。我花了一部又一部电影试图超越它,来创造更多的视觉效果,因为我喜欢差异性。但是,你只能做这么多。电影必须是属于角色的。
记者:在所有的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是恩尼斯在片尾拜访杰克的父母那一幕。你怎么去设置那种情绪呢?
李安:嗯,这是一踏上拍摄现场我们就会考虑到的。那是我在电影里最喜欢的一幕。这是一个非常坚忍的场景,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不在的人的场景。杰克·吉伦哈尔很生动地演出了这一幕,关于这个所有人都失去了的人的一幕。我的视觉灵感来自安德鲁·怀斯,还有丹麦画家威尔海姆·哈姆休伊的那些光秃秃的,白色的门。因此,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合适的房子,合适的空间,当然,这是我的美工设计师朱迪·贝克尔的任务。为了拍摄那一幕,我使用了曾经在《绿巨人》中用过的风格。我用两架摄像机拍摄,从两侧拍摄演员,然后更换镜头,并且再拍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方式。当你在一起编辑时,你可以对某些反应,情绪有一定强调。这样拍摄可能会让一些演员摸不着头脑。但是希思·莱杰,彼得·迈克罗比和罗伯塔·马克斯韦尔都没有,这让我很喜欢。那一天很奇怪。我正想着需要一些阳光,阳光就来了,我还记得自己走向现场,觉得今天会是很棒的一天。这样的场景,演员和他们的面孔让这一切完美起来。
怎么与演员的合作:

图为《色,戒》工作照
记者:在选角时你经常会混用新手演员和老演员,你是怎么样指导演员们,让他们演出你想要的感情呢?李安:这事情我可以说很久很久,因为每个演员都是不同的,每个演员都像是一座你必须爬过的山。当然,没有任何事情是容易的。我认为某个人全神贯注投入非常多的精力来制作电影时,这些主角会成为导演的重要部分,所以你会把自己和演员融入到一起,并且演员们也知道这一点。你在看着他们,他们也在看着你。而且我也会思索,要怎么样才能把他们变成我心目中的那个人?他们也在看着我,试图找出我想要什么,这样他们才可以演得出来。我说过我跟摄影师,美工设计师,作家和制片人的关系,我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了他们。但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把自己最好的部分给了演员。这并不代表我是演员的朋友,实际上我基本不跟他们来往。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冷酷。但是我只干自己认为有必要的事情。我只是为了把我想要的东西和艺术的时刻表达出来,并且让它们永远凝固在赛璐珞上。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非常不简单,制作电影对我来说是相当神圣的事情。我觉得演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记者:让新人和老将同场飙演技有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李安:让他们同时出演肯定会出现很多困难,我拍摄《理智与情感》时,凯特·温斯莱特只有19岁,这是她的第二部电影,所以有些事情对她就会比较困难,比如说应付摄像机,还不能意识到它。当然她现在已经可以掌控这一切了,只是那时她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大好。但是对于艾玛·汤普森来说,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艾玛的演技是很纯熟的。她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次就表达四五层的情感。但是,尽管凯特相对还比较稚嫩,她却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可以让观众不自觉地为她担忧。这对凯特来说很简单,但是对艾玛来说就比较难了。在这部片中她们出演姐妹。
记者:当你要和演员们开始合作时,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李安:首先,你必须让自己意识到演员的呼吸和感觉。排练有助于让你进入这一状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拍摄的时候。通常我会做两三个星期的排练。这个排练并不是要像真正拍电影一样。我认为电影演员不会在排练时倾尽全力,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排练时就倾尽全力,在正式拍摄时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么做了。如果他们在排练时有所保留,那么你真正想要的那些品质就会保留到正式拍摄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排练就是要帮助我们来看清演员。而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要亲自看到角色在演员之中成形的过程,演员是如何培养这个角色的味道而且让角色与其他人发生化学反应。到了现场,我们都必须和摄影机打交道,而且都会拍摄当下,你必须去思考和感受。因此排练时候的效果并不是真正演出的效果,而只是一种共同思考的方式。
怎么对待“导演”这一职业:

图为《少年P的奇幻漂流》工作照

李安与伯格曼
记者:你身边有这么多活动,你又是怎么看待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呢?李安:我认为电影是一种人工介质。它不是生活。它不是真实。但它肯定有着自己的生命。有着你必须膜拜的电影之神。有时候你必须放弃每个人的意见,只听电影之神的声音。我会首先去做很多事情,但后来我就有点像是成了观察者,并且会决定应该走哪条路来符合电影之神的意图。我认为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道路,我告诉我的演员和剧组成员,这无关我们,也无关我自己。我们都是电影的俘虏。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试着来调整大家,带来团结。
记者:你来到现场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李安:我在拍电影时会在早上做好计划,然后演员们回来化妆,我给出分镜头表。我会与助理导演,摄像以及美工部门一起协商接下来的场景。我们准备好场景之后,就会继续探讨细节并且将它们逐步改进。再接下来就是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直到你确定想要哪一幕。
记者:一个镜头要拍几次?
李安:大概要拍六到七次,一般来说,很难超过十二次,但是也不会少于三次。拍《色戒》时,只要超过五次,汤唯就会变得注意力涣散。她非常情绪化,非常容易波动,因为她是第一次拍电影嘛。她会在现场立马融入情绪,然后就走神了。对于其他经验比较少的演员来讲就大不一样。比如说《色戒》里面的王力宏,或《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德米特里·马丁都是新人电影演员,他们的表现会一次比一次好。有时候他们的第七次就会比第六次好。但在同一个镜头里,也有可能直拍到第五次都不如意。不过,也会有理想的演员。比如说,《色戒》里的梁朝伟或《冰风暴》的琼·艾伦,不管拍上多少次他们的表现都是很完美的。所以各种情况都会有。有很多混合,配合以及平衡要做。
记者:在《色戒》里你把极度浓烈的感情与非常露骨的性爱场面相结合,这样是不是很难达到合适的平衡呢?
李安:是的。这两个角色都试图杀死对方。他是逼供者,她是诱奸者,我找不到比这更加浓烈的感情了。我会和演员们说到与妻子家人都不会接触到的题材,因为我与演员们分享最为私密的空间,对他们也都非常直接。我们就是从这些材料之中创造出自己的艺术并且在那个层面上有所连结。我是在用这些角色来暴露我自己。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经历。至于性爱场面,我认为我们是在突破表演的某些界限。你必须监督表演,并且创建一个境遇,让你反思在你面前发生的所有一切是否真实。那就是一个导演能与演员们享有的最终极的体验。但那也是非常可怕的。这部片拍完以后我们都有一个月很不舒服。它就是有那么激烈。拍完这部影片之后,生平第一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演员们从这部片子里拉回来。我还和汤唯有着联系,帮她从那个角色里解脱。而在过去,我并不认为这是我自己的工作。
记者:你跟演员们通常维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李安:我不知道演员对我的感觉如何。当我第一次执导英语电影还摒弃了蛮多东西的。因为我的英语讲得很不好,所以会给出非常直接了当的指示。一开始演员们都很震惊,到后来他们懂得这是因为我的英文说的很烂,也不知道怎么把英文说得更好,所以都容忍了我。但是后来我的英文越说越好,也就有所收敛,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变得更加文明。我在拍《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开始有所放松,有点是因为拍摄《色戒》时感情过于浓烈了。抛开想让题材更加正面向上不说,我个人决定要变得更加温和友善,而且确保大家都更加开心。
面对“电影市场”拍片有什么计划:

图为《少年P的奇幻漂流》工作照
李安:我们在亚洲市场的经历相当有趣。拍摄《卧虎藏龙》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拍武打片。但同时我又想拍摄更高级的武打片。我并不想拍摄童年看的那种香港B级武打片。后来我们就把这部片子拍成了A级片与B级片的结合。这种做法在东方市场并不是很受欢迎,虽然我们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新方法在这里更受到欣赏。但是《色戒》的反响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东方它造成了一种巨大的文化现象,但是在西方它却并没有收到什么反响。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西方观众跟那段历史没有直接联系,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东方观众更加能够接受它的悲剧性,而不是西方观众。
记者:中国的观众又是什么样的呢?
李安:中国内地电影现在才要真正开始起飞。这是一个新的市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市场。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制造自己的中庸式的电影。虽然盗版侵权无处不在,但是观众们仍然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你可以看看在中国大热的片子,就算是我,也很难了解为什么中国观众会喜欢这些东西,为什么又不喜欢某些东西。中国观众的人数是美国观众的四倍,也就是说,就算某部影片只在一个城市放映,也可能会回收上亿的票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记者:鉴于市场的复杂性,你觉得你拍摄的这些影片还会有市场空间吗?
李安:我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区域。我拍的电影可以说是大型的小电影,并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而且我会去拍那些自己想拍的影片。在国际影界方面,我认为在美国以外有很多有趣的电影。而且美国的艺术工作室出品的影片常常被定位为低成本影片。除了这个我们还有好莱坞电影。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很多可以被称为“墙头草”的电影。现在的电影是两极分化非常厉害的。有很多艺术成就已经非常高的导演们会得到更多的钱来拍摄更多影片,但并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这样。
记者:你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根据扬·马特尔的书改编的。它讲述了一个少年与一头斑马,一只鬣狗,一只猩猩和一只老虎被困在救生艇上,在太平洋漂流的冒险故事。这听起来似乎很棘手,而且似乎需要许多准备工作。
李安:2001年我初读这本书时就被迷住了,但那时我并不认为它可以被拍成电影。后来我开始拍摄《创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福克斯2000来找我并且说,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可以启动了。我认为这部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层面的难度。它包含了动画,所以视觉预览将开始发挥作用。我不喜欢视觉预览,通常也不做故事板。有时我做,但不会全部按照故事板来。为什么你要跟着故事板来拍镜头,而不是去尝试找到某些东西,并且利用它来为你的影片服务呢?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导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拍摄昂贵的镜头时,你必须做一个详细的计划。你不敢随便采用平常的计划,怕输不起。这十分令人兴奋,这就是电影制作,电影制作之中从来不讲规则。
探究《盗梦空间》《蝙蝠侠》系列导演诺兰的电影世界
奇异旅程——《魔戒》导演彼特-杰克逊谈在电影之路上走得多远
专访马丁·斯科塞斯,解读电影最不可缺少的元素
专访斯皮尔伯格:怎么讲一个“成功”的故事?
专访《异形》导演雷德利·斯科特
专访《泰坦尼克号》《阿凡达》导演卡梅隆
DGA专访老爷子伊斯特伍德
专访《楚门世界》《死亡诗社》导演彼得·威尔
更多电影人专访/院线片“观感度解析”请见:观影频道
本文为作者 分享,影视工业网鼓励从业者分享原创内容,影视工业网不会对原创文章作任何编辑!如作者有特别标注,请按作者说明转载,如无说明,则转载此文章须经得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影视工业网)及本页链接。原文链接 https://cinehello.com/stream/24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