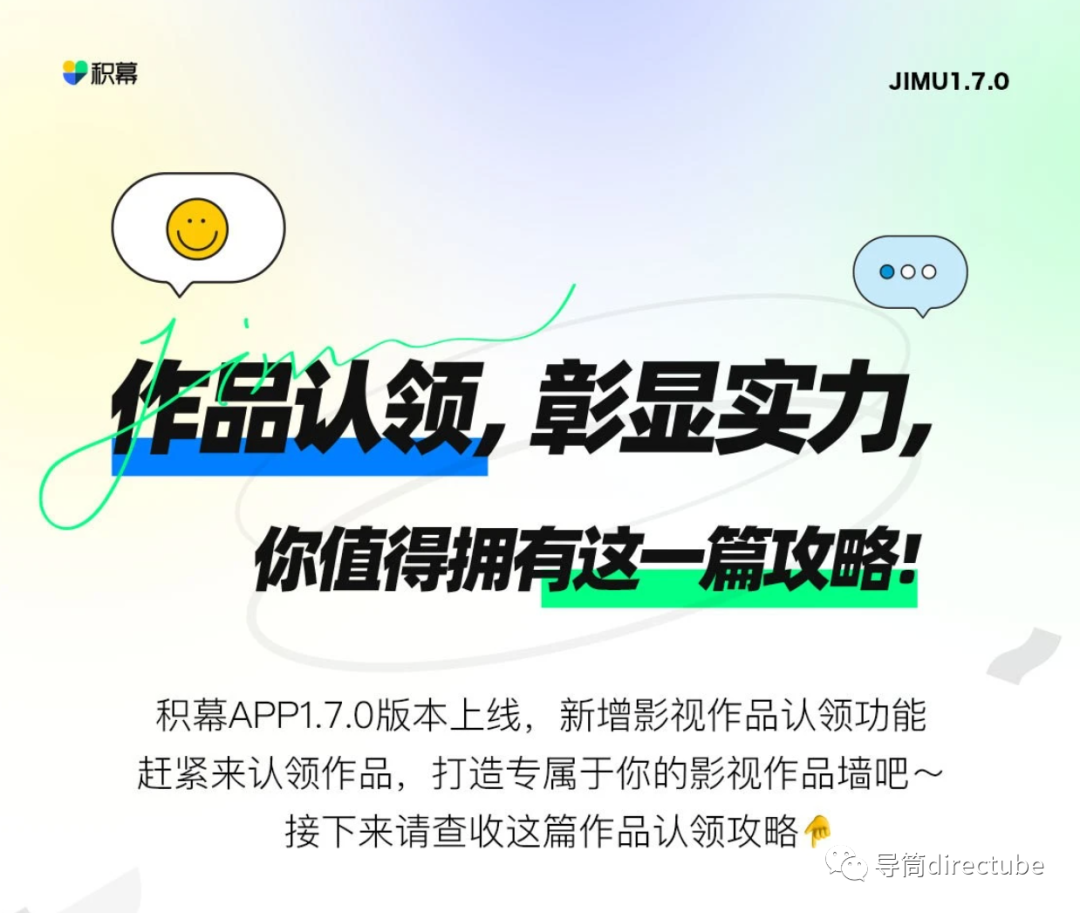李安谈《色戒》:观众的想象最重要


我先替大家丢几个问题。导演早起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都是原创剧本,导演甚至自己参与编写,但是从,理性与感性》后,您不断挑战文学,甚至面对公认最难改编的张爱玲。可以给我们谈谈这当中的转变,以及挑战张爱玲的感受吗?
李安:我是在拍这个片三四年前看了这本小说,看到小说结尾王佳芝叫易先生快走时,我觉得很震惊,我对张爱莲感觉非常愤怒(全场笑),她怎么可以这么写呢?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愤怒,我只是觉得张爱玲怎么可以这么写东西,挺不像她。
这篇小说挺诡异的,好像是在模仿电影,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拍成电影。她文字这么好,你去follow文字当然是死路一条,所以连试都不要试。但是这篇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不过当时没想要拍,只是觉得愤怒,真的是...(全场笑)抗日战争是中国神圣的一场战争,而且用色情小说的方式....我从不觉得张爱玲会写情色,但是这本我基本上觉得是黄色小说,而且很不诚实,拐弯抹角的地方很多,....绕着我又绕出去。
中间我去拍了《绿巨人》,《断背山》,也没特别想,但是时不时张爱玲就好像来缠我,我觉得很奇怪,老实说,我觉得拿到奥斯卡好像就可以拍了(全场笑),舍我其谁?!我必须挑战它,你们年轻不晓得那个时代,起码我听父母那代说还有点印象,再不做,再不做,这段就在中国历史消失,就这么一个想法。但我其实很不愿意去拍,因为它非常大逆不道,可是我又感受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共业,很像一个鬼缠着我。
越不想做,越觉得奇怪的东西,相反越有吸引力。基本上我很像王佳芝啦,是个好人去拍坏人,好女孩去演坏女孩,结果坏女孩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只有透过演戏才能触摸到不敢面对的自己。这个主题对我非常重要。
还有个地方非常震撼我,我18岁跟王佳芝一样第一次站上舞台,魂好像出窍,我觉得我属于黑暗的地方,因为灯打在我眼上,什么都看不到。也是在第一次演完戏,拆了台,跟同学出去唱歌,下着小雨,跟小说写的一模一样,我感觉的戏剧的力量,我感觉我就是王佳芝....

拍进去以后,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我的心好像王佳芝,我的头好像邝裕民,我的那个...那个....不好意思讲,好像易先生(全场笑)。小说虽然只有短短30页,但挺诡异的,以张爱玲的才气,几天就可以写出来了,但是她花30年时间,其实在重写,用修改的文字掩藏真正要写的东西。我想她心里害怕,怕人家不知道,又怕人家不知道。我拍的时候也体会到这种心情,有点大逆不道,又忍不住要做,跟我拍其他片不太一样。
我以前的电影自己写剧本,因为刚刚出道,没人给我剧本,只好硬着头皮写,等到拍出名了,大家就给我东西,好多东西,何必自己写(全场笑)。因为我知道的有限,生活有限,拿到世界名著很快乐,学习各种语文,社会,尝试各种电影形式,我觉得拍这些电影真的是我最好的电影学校,希望我永远是个电影系学生。但我最新在准备的片就是自己的想法,我请别人写,但这次不是改编。

李安:那其实是我的纯真年代,看起来你们很多人还在纯真年代(笑)。那段对我来讲挺重要的,不过王佳芝的经验在香港,我是在板桥(台湾艺术大学)。我希望把60年前香港还没发达的场景、味道做出来,但现在香港并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反而马来西亚像点,把屋顶用电脑修一下就可以,片中的电车也是用汽车改装的。
闻天祥:《断背山》跟《色,戒》的原著都是篇幅非常短的短篇小说,但您完成的影片长度却比一般剧情长片都长,全都超过两小时;您好像在帮它们写注释、做延伸。但比起来,《断背山》的观点比较接近原著,即使结笔的手法不尽相同,观点、态度倒是挺一致的;可是看《色,戒》却觉得你跟张爱玲的大相迳庭。
我觉得王佳芝的凝视非常有意思,我在小说没看到这部分。比方说,他们迁校去香港的路上,在女同学的喧哗声中,我们看到王佳芝的眼神望向穿着白衬衫、很帅的邝裕民,而邝裕民正在凝视行进中的阿兵哥;后来在排戏演戏时,王佳芝的凝视也很清楚。我不断在猜测,你安排她父亲带弟弟去英国,把她留在中国,好像抛弃了她,然后她似乎在邝裕民身上看见「理想男性」的典型,但后来「杀汉奸事件」又好像摧毁了这份寄托。相较之下,她理应要恨的汉奸易先生,好像更有真性情。我觉得电影里面有好多读小说时没看到的,这是你气愤张爱玲而改写的地方?或者你觉得是她藏起来的部分?
李安:我觉得是她藏起来的,我气归气,可是我…(全场笑)进去以后一直在想,王佳芝有很多张爱玲的影子。因为这篇写得很“贼”,不能完全相信。我不敢讲其他小说,因为我在张爱玲炼狱里活了一年多,有很深刻的体会,我没办法跟张爱玲专家辩论,可是我真的体悟到她讲的是这么回事。
你刚才比较了《断背山》把小说的其他地方补足就是这部电影,《色,戒》不是这么一回事,有点狂想。演话剧演到去杀汉奸,怎么有这种事?!真的付诸非常写真的影像,可信性值得怀疑。这其实是心境的写照,很多伏笔、假笔、歪笔,合不起来,你进去后要想怎么圆这个故事。
大家说她后面写得很绝望、很冷酷,但其实我觉得她很需要父爱,所以我用摇篮曲、很多方法来圆这个东西。当然这是我跟张爱玲的神交,我不是做学问的,没办法引经据典,只是将心比心;但我觉得她可能在纯真丧失时受到很大打击,对胡兰成、那个时代有爱有恨。最重要的一点,她用女性的性心理学,来对抗父系社会下对日抗战这么神圣的事,当她把易先生放走时,小女子小小一句话,好像把几千年父系历史结构抽掉一个东西,突然瓦解。这是一个小女子的力量,性欲的力量,是个很不道德的力量,可是又很巨大,让我们深深反省。
这力量是很可观的,我不能用道德力量来解释这小说,我觉得这小说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小说,有些不是很高明的比喻,要不是她不会写,要不是故意写不好,让我这种人钻进去吧(笑)。我说不上来,总之我觉得导这部戏时很焦虑,转不出来,心情大受影响,需要用剧烈手法,得用性和毁灭来面对真实、底层的东西。我也不是神经病,我也很正常的一个人(全场笑)。
包括我三个主要演员也非常投入,他们还回头来安慰我。记得有天我哭到不行,梁朝伟过来对我说:「导演啊!我们只是露个皮肉,你要保重。」(全场大笑)梁朝伟被我折腾成那样,还反过来安慰我,拍完后我们四个都生了好久的病,好像大病一场。这东西虽然我不愿意讲,但跟张爱玲一样,又怕人不知道(笑)。我不是张爱玲专家,只是有种神交的感觉,隐隐约约,觉得她就是这样写。

李安:小说这样写易先生,当然很糟蹋他,我觉得因为她很恨胡兰成(全场笑)。只是她不爱胡兰成,怎么把他骂成这样子?骂他鼠辈,这「鼠辈」我觉得是胆小如鼠,不是尖嘴猴腮的鼠相,他长得很清秀。拍那么绝情,电影怎么看呢?!把易先生写这么绝情,可能是她的火气吧?她那么恨胡兰成,我没有,没必要跟她那么去(全场笑),一个电影没有感情没办法看。所以我觉得她的感情很重,是用反笔写一个很动人的爱情故事。
闻天祥:这部片子有非常清楚的历史跟地域特质,但您合作的编剧、摄影、剪辑、音乐都有外国人,他们要怎么进入这个世界?你要跟他们解读这些历史环境吗?
李安:他们需要了解。要拍这样的电影,中国电影本身是不够用的。他们有film noir(黑色电影),我们没有film noir里的俏皮台词;前半段我用了很多melodrama(情景剧),言情剧的东西,但这又不合西方的film noir。他们来拍我的电影,当然得经过我的诠释。比方说我用James Schamus(《色,戒》编剧)来加强编剧口白的部分,中国语言不太有斗嘴,张爱玲是很西化的人,她是个电影迷。就我的眼睛来看,这篇小说至少抄了三部片,影像上的shadow(阴影),还有intercut(对切),这些其实是用电影手法写的。因为是学电影的,所以可以拍,只要还原一下。

闻天祥:如果我们从当中找一个人继续深入聊,比方法国音乐家,他作的曲子听起来有点中国风情。这是他本来作曲风格就有的,或者你有帮他进入这个时代氛围?
李安:其实我不跟他强调中国风,反而要他听像《豹人》Cat People(1942)这种老好莱坞片,中国电影当时刚起步也都在学西方。他对乐理很清楚,并不困难,例如我要求那个摇篮曲,他就做得非常中国。其实《断背山》的音乐我觉得也很像中国音乐,用留白、空间的方式。西部片其实也非常中国…这些东西想穿了,其实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呼应。
我也不晓得,用西方人来做中国片的话,绝对不会叫他们去学个五音阶,我就跟他说中国一点就好了。反正听听嘛,不像再换。

李安:要调和。先观察、排戏,再调和。不光是经验问题,他们本来就是不同的演员,表演方式也不同;我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让他们在一个电影、不是三个电影。
指导演员也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他们的启发,一个是对他们的捕捉。新演员有个好处,很纯真,很努力的时候,样子很动人,梁朝伟就没有办法(全场笑);层次的话,新演员就很困难,像梁朝伟这种戏精,我说他已经变「戏仙」了,就很容易。各有长处,看你怎么调和,用摄影机捕捉,跟他们对话。任何表演方法都不可拘泥。我觉得表演方法就是学来知道怎么丢掉,像我们做导演的,什么方法来,就要知道怎么去应付。
选汤唯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戏情色很重。我第一次看到汤唯,很像我高中的国文老师、历史老师,有那个味道,现在中港台很难找到这气质。所以她本身不是那样,演这样的戏就不怕。如果她本身太上相,我就会担心走到太色情。选她也因为她蛮天才的,不是说她会表演,而是她会相信,你给她一个指令,她会相信,这不是导演的自我获得满足(笑)。像我最近选《少年Pi的奇幻漂流》那个小孩就很幸运,告诉他一个状况,他在里面不会跑出来,这是做演员最大的天份。
梁朝伟比较难这样做,进进出出太多次。梁朝伟很专注,他是导演梦想的演员,不用担心他,反而有时要把他磨到没力气去演,有时我真的很折磨他,他也知道我在干什么,就比是我还是王家卫比较会磨,看谁比较狠(全场笑)…他也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也知道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东西。已经13条了(拍13次),已经很不人道了,我说看起来你还有点力气。把他磨到像第一次演戏,从完美到不完美,连他都无法控制时,就会很动人。对于这么好的演员,我会去榨他。
汤唯就不一样,不能把她的纯真磨掉,因为这是最动人的。她相信王佳芝是自己,看电影看到爸爸不要她了,真的哭了,摇都摇不醒。汤唯的个性这么容易相信,人就容易漂浮,比较情绪。我就先拍汤唯这边,拍完再去拍梁朝伟,磨他的戏。比如说拍汤唯要被抓了、看戒指(藏有毒药)的表情,拍了13条,每一条你要告诉她新的意义,都给她一样的,她可能就散形了。
王力宏的话,演戏就没有,但他是个很努力的人(全场笑)。他跟汤唯我都后拍,他是在练,很稳定的进步,就是一个金牛座的人。很难讲啦,要讲挺长的…(笑)
李:我请了台湾的樊光耀,口条很好,三个人都有训练。那时国民政府定的国语的不是现在大陆讲的北京腔,而是以北京话做底,像小时候听的播音员、看的国泰电影。
观众2:您好,见到您很激动,因为您是我超喜欢的导演!(台下鼓噪:告白了)我今天从台中专意回来看您。你在拍「父亲三部曲」前很困难,也在一次采访提到,拍电影有很多外部、内部压力,但您都撑下来了。您在奥斯卡说:「感谢电影之神」。我很想知道是什么让您坚持到现在。我是一个学生,从大陆来台湾学电影,我想从您身上得到答案,因为我以后也想坚持现在这种热情。
李安:我老实讲,在我身上适用,在你身上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短处,要自己去摸索。在我还没「开张」以前的六年,不是我坚持,是我没有选择。我拍电影就很灵光,不拍电影就很不灵光,非常明显。常常有人说,你要怎么鼓励我们啊,我说这种行为千万不要做,因为我现在看到在做的,都是明明没有希望还是要做,这种人才是拍电影的人。如果你喜欢安全感就不要做这行,不管怎样都没有安全感,你要很爱冒险,喜欢新鲜的东西,喜欢影像。你现在在学,代表你有热情。

电影这东西很奇怪,跟它有缘,什么都有可能,不要想太多现实。当然也有些人因此吃很多苦,我是很幸运,真的,有比我努力、聪明、有天份的,不见得有机会。我太太不管我,她上她的班,我在家发我的呆(全场笑)。拍片在外面跑,她自己带小孩活下去,也不喜欢参加我的活动。她平常不穿裙子、高跟鞋这些,奥斯卡来了,没办法,就穿了,就去了,化妆嘛,随便啦(全场笑)。我想我的命里也有一点缘份吧。对电影的热爱很难形容,我也不是意志坚强,只是很喜欢,不做出来很难过,弄不出来也不晓得怎办,就继续弄,其实很简单。
观众3:请问您跟Tim Squyres(李安常用剪辑)的合作关系?
李安:大部分都问James Schamus(李安常用编剧),没人问Tim Squyres(李安常用剪辑),你是第一个问的。我在拍《推手》时,虽然在美国拍,但这是完全为中文世界拍的,得找个中英文通,找到一个女的,但她生了小孩得养,我们付不起,就开始interview,第一个碰到的就是Tim Squyres,就僱用到现在。
他是一个脑筋很清楚的人,很好的editor。《推手》全部是中文,但他剪出来完全是对的,我不晓得怎么弄的(全场笑)。不光选对的画面,哪个接哪个,哪句话接哪句,他都能做得一格不差。也没别人雇他,一直跟我做,直到《理性与感性》才做英文片。他是个美国人,现在中文只会说一句「谢谢」吧。
我们的关系最密切。电影有一半时间在后期,有特效会更长,会到一年、一年半。这20几年里等于有一半时间,每天跟他在一起10到12个钟头,我跟太太或所有人都没讲过这么多话。他除了是个很好的剪接师,也是个科学家,理路非常清楚。他的家学很好,都是优秀科学家,像他哥哥主持火星计划。他跟我是很好的搭配,因为品味非常相反,而且第一天就认识我,不太甩我,直话直讲。两个人关在一起,若是一言堂会常常犯很多错误,有个人商量其实非常好。
每部片都他剪,除了《断背山》。很不幸的,我跟他说拍完《绿巨人》要休息起码一年,他就接了《谍对谍》(《辛瑞纳》),但过三个月我受不了了,就继续拍。他看到初剪时,气死了(笑),差点跑去撞墙;最惨的是后来得奖,一直有人打去(电话)恭喜他(全场爆笑)。

李安:别的片子怎样跟我没有关系。摄影方面,我用Claudio Miranda(少年派的摄影师)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是David Fincher(大卫·芬奇)的人,一个很好的导演,所以艺术上我很信任他;这片是用数位(数字摄影机)拍,我以前没拍过,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因为她拍《班杰明的奇幻旅程》拍得非常好,在我们之前他也拍了部真人3D片,当时没多少摄影师有这种经验。所以总体加起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老实讲,我觉得他的打光还是比较传统,我希望将来还能突破。
作曲其实算是我的老搭档Mychael Danna,跟我做过《与魔鬼共骑》、《冰风暴》,在做《绿巨人》时因为不合适换人,我这次想把他抓回来,因为他很合适,印度音乐是他的专长。我做《冰风暴》时想做70年代东南亚风味,但当时没这种东西,他就做出minimalism(极限音乐)的效果,当时很流行。所以我知道他对印度下过功夫,太太也是印度人,也为很有名的印度导演Mira Nair作过曲,总体加起来很适合。他还是加拿大北方人,讲究精神生活,非常喜欢探索。

李安:随缘(全场大笑)。再补充一下,我最近发觉,过去都要给自己找个理由,因为拍了就有人问,我就尽量想想回答。但我最近觉得拍了一个片,就想逃离一个片,不晓得在躲避什么、逃离什么,不晓得为什么,很不喜欢被人定位。也可能我无法给自己定位,也可能我是个很用功的电影学生吧,有这么多类型、题材。就跟看风景一样,为什么每次都去同个风景区?再露骨一点,婚姻要忠实,但拍电影不需要(全场笑),像交女朋友一样,图新鲜。
观众6:终于看到未删节版的《色,戒》了,非常高兴,我看完后觉得这是个爱情电影。我有三个问题:第一,这三个主角中,导演您觉得谁最幸福?谁最痛苦?第二,这里面有没有您的爱情观?第三,您在现实生活中怎么看待爱情?
闻天祥:这好像应该要问吴若权(台湾作家)才对(全场大笑)
李安:三个问题可以一句话回答:我电影里拍的都是我生活上做不到的事(全场爆笑)。当然有很多我的感情寄托,但跟我的生活关系不大。这三个人都有我的一部分。他们在拍片时也看出来了,我就看他们怎么演,观察他们在演我的哪个部分,所以拍床戏非常痛苦,不晓得哪个部分打哪个部分…
不只爱情上困惑,对自己的存在也有。因为电影是个虚相的东西,可是在我们的心里又是比实相更真实的投射,虚实之间让我觉得人生很困惑,我真的存在吗?或怎么一回事?我眼睛看到的是什么?还能相信吗?我在里头打转。我拍电影想把最好的、最真实的解剖给观众看。
拍电影是一个容器工具,燃烧自己,让观众得到一些启发,不是我启发他们,是他们看完有所启发。我总觉得我的生活很刻板、很无趣,但在电影里,尤其是爱情戏,感觉很浪漫。你讲得没错,这是个很浪漫的电影,对我来讲,能浪漫好像很不容易。我拍浪漫就这两部吧,其他没去讲爱情的东西,不像《断背山》跟《色,戒》连着两片谈爱情。也是有投射,不过我生活上没什么精彩的故事(笑),我很期待有精彩故事,但现实生活不是那么回事。
闻:谢谢导演今晚动人的分享。请问导演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满场观众说的?
李安:这电影其实也没什么结论。电影对我来讲就是一直拍,直到没人看,拍不动了,拍烦了,就这么回事…总体来说,拍了这么多年,好像电影的奴隶,不是电影的主人。今天这么多人挤进来,好像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答案,其实没有,答案在你们心中。我电影拍得多好,也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电影最好的不是在做一个表达、告诉你一个故事,而是你在观众心里激起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我常常跟年轻的外国演员讲,我自己的儿子也要做演员,我直接跟他们讲:「其实你并不重要,我也不重要,观众的想象最重要!」
当你演得那么足,就不需要观众投入了。在半知半解、半到不到,观众隐隐约约比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知道还多时,是他们最投入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最可贵的地方。不是说我们是艺术家,你们来吸纳,而是你们在脑筋里有什么东西。既然我有这个天份,就继续做,就这样。电影要有观众看、有回应,电影的活动才叫完成。电影真是蛮好的发明,功德一件,谢谢大家(全场掌声如雷)。




「导筒」微信号 directube2016

推广/合作/活动
加微信号:directubeee

本文为作者 分享,影视工业网鼓励从业者分享原创内容,影视工业网不会对原创文章作任何编辑!如作者有特别标注,请按作者说明转载,如无说明,则转载此文章须经得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影视工业网)及本页链接。原文链接 https://cinehello.com/stream/14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