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国际主流纪录片的“故事化”转向
“后真相”时代
国际主流纪录片的“故事化”转向
作者:佟珊
原载:《当代电影》2023年第11期
概览全球票房排行榜或者国际电影节的获奖名单,不难发现近年来广受好评或获得票房成功的主流纪录电影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即追求讲述精彩的故事。本文将这一趋势视为纪录片创作的“故事化”转向,试以“当代叙事纪录片”来指称这些作品,将其视为纪录片美学范式的转变,结合纪录片理论,总结其美学特征,并以近年获奖纪录电影为例加以阐释。其次,本文将这一故事化转向与国际纪录片制作环境和生产机制的变化、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后真相”境况结合起来分析,试图阐明其背后的逻辑与关联,进而对故事的主导地位提出批判性的思考。
关键词:国际主流纪录片 当代叙事纪录片 故事化 后真相 纪录片美学
概览全球纪录片票房排行榜或电影节的获奖名单,不难发现近年来广受好评或取得票房成功的纪录电影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即追求讲述精彩的故事。换言之,精彩的故事日益成为主流纪录电影在当下国际市场获得融资、传播和观众注意力的关键要素。纪录片导演布雷特·斯德瑞(Brett Story)认为故事——“在传统意义上对预期组成部分如角色、情节、背景、冲突和主题的线性排序”——已经成为当下纪录片领域的霸权形式。英国《卫报》刊于 2021年的一篇报道则指出,过去 15年的票房冠军如《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2005)、《艾米》(Amy,2015)、《孪生陌生人》(Three Identical Strangers,2018)、《徒手攀岩》(Free Solo,2018)都采用了类似的故事结构。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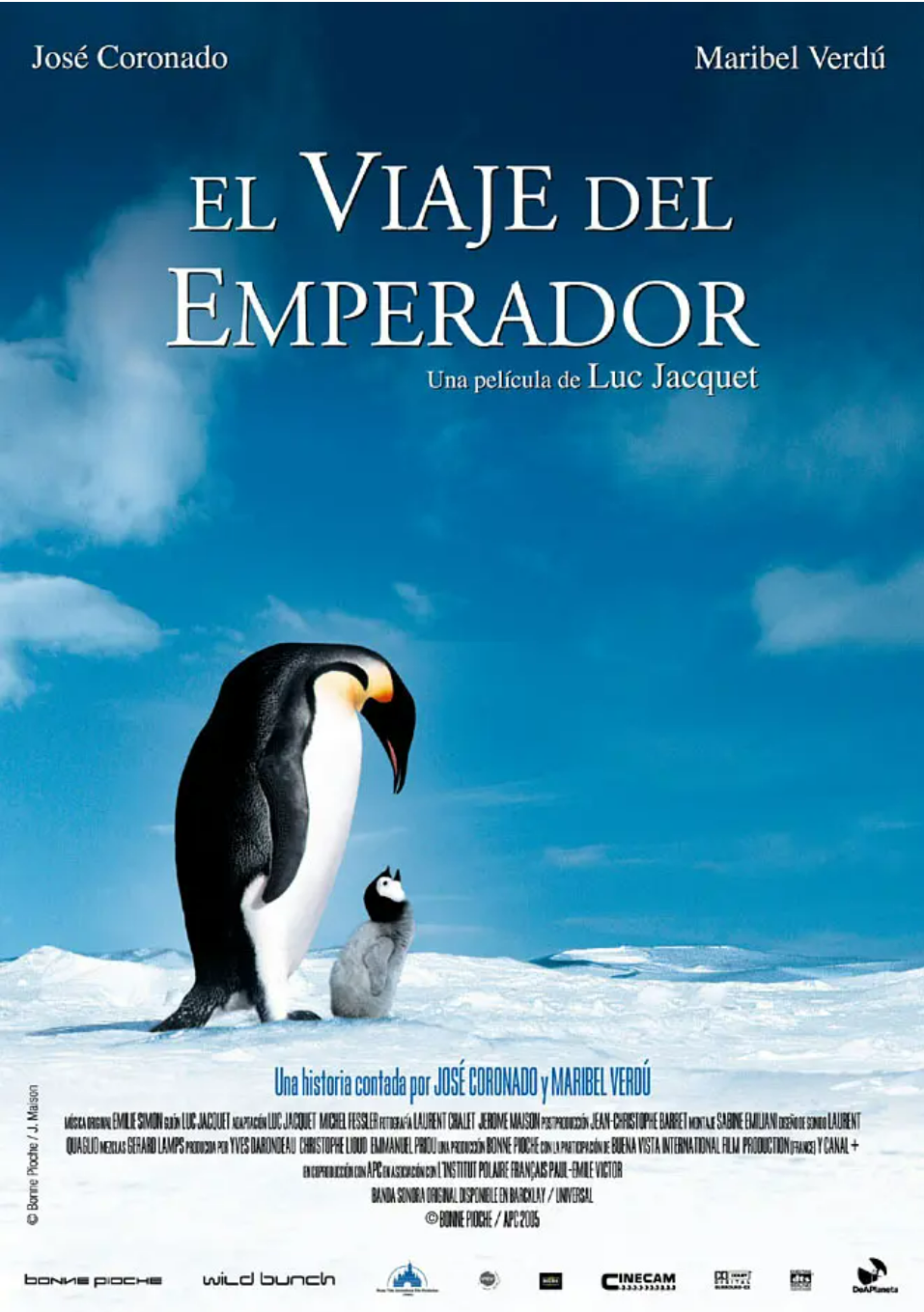
《帝企鹅日记》
尽管从 2000年初起,中文学界就不乏针对纪录片“故事化”的讨论,不过这些文章大多探讨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将情节、悬念、搬演等剧情片手法应用于纪录片创作的问题;或是以叙事学理论及概念对成功案例进行分析,且基本都对故事化持肯定态度,呼吁国内纪录片创作超越“纯粹记录”的处境,推动其向大众化与商业化的转型。与之相较,本文的研究对象、借用的理论资源、研究问题与论点都有所不同。本文以近年的国际主流纪录电影为研究对象,聚焦这些作品呈现的故事化趋势,结合纪录片理论,总结其美学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打破产业话语中有关故事的跨文化普世性的迷思,试图追问:何种制作环境与机制导致了纪录片越来越倾向于讲故事以及采用特定的美学形式?其中,提案作为国际纪录片的重要生产机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讲故事的纪录片如何呼应了“后真相”的境况?透过上述问题,本文考察纪录片的故事化转向与特定制作、传播环境的关系,并指出故事形式主导纪录片创作可能产生的潜在问题,以提出批判性思考。
一、当代叙事纪录片的界定与美学特征
谈及纪录片叙事,纪录片学者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认为纪录片必然存在叙事;纪录片的叙事不仅不与其对真实的主张冲突,并且是决定纪录片创造性的关键。此处,温斯顿指的是广义上的叙事——“一种文本内部的、文本与消费者之间的组织方式”。依照这一观点,不同形态的纪录片都包含一定的叙事元素。不过,本文所讨论的“叙事纪录片”主要指以人物或事件的发展变化构成故事这一类型:它们不仅包含如人物、背景、事件、冲突与悬念等叙事元素,且叙事线索由人物行动所推动的事件构成,叙事结构建立在事件的因果关系之上。这一类型或可追溯到被视为标志纪录片诞生的、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the North,1922),并随着电影讲故事技巧(如视点叙事、平行剪辑、连续剪辑技术等)的发展而逐步演化。

《北方的纳努克》
聚焦于当代国际主流纪录电影对精彩故事的追求,笔者试以“当代叙事纪录片”来指称这些作品,将其视为近年纪录片创作故事化转向的体现与结果。尽管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时间来划定纪录片故事化转向的起始,但根据下文论述,这一趋势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的纪录片商品化、纪录类型娱乐化密切相关。除了继承观察式影像的传统外,当代叙事纪录片也一定程度结合、吸纳了解说模式、自反模式的表现手法,是从传统纪录片形式演变出的一种新的混合模式,并呈现以下美学特征。
(一)观察式影像作为制作方法与影像风格
当代叙事纪录片很大程度上继承与吸纳了观察式影像的传统。在制作方法上,当代叙事纪录片往往依赖长时间的跟踪拍摄,捕捉人物和事件在时间中的变化,以构成叙事线索;在影像风格上,当代叙事纪录片多采用观察式风格,制造出摄影机与创作者不在场的假象,让拍摄对象彼此互动,营造出如传统剧情片一般的、透明直接的效果。此外,观察式影像还会造就一种强烈的现在时效果,即便事件已经发生、结局也已知,如纪录电影《泰国洞穴救援》(The Rescue,2021),影片依然可以借助现场记录的观察式影像,赋予事件一种“现在时”感,带领观众回到事件发生现场,创造出一种戏剧性。

《泰国洞穴救援》
不过,当代叙事纪录片也常常会打破观察式影像营造的“第四堵墙”般的叙事幻觉,吸纳互动性、自反性的手法和表现方式,如拍摄者在镜头外向拍摄对象提问;或将拍摄过程、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关系纳入影片,构成叙事线;甚至拍摄者自己就是影片主角,将摄影机对准自己以及朋友、家人等。这也说明,当代叙事纪录片并不严格拘泥于观察式影像的创作理念(即不受干扰的纯粹记录),而更多将其作为一种制作方法与美学形式吸纳进来。
(二)多采用三幕式叙事结构
在叙事结构上,当代叙事纪录片比早期观察式纪录片更具整合性。观察式纪录片,因其长期跟拍的创作方式往往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大量琐碎、无关联的素材中建构起线性、有逻辑且可延展的叙事框架。早期的观察式纪录片极力避免采访和解说,力图以影像本身建构叙事和意义。如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的《初选》(Primary,1960)或梅索斯兄弟(The Maysles Brothers)的《推销员》(Salesman,1969),其叙事结构较为松散,且较多保留了影像的暧昧性和多义性。与之相较,当代叙事纪录片展现出更强的叙事整合倾向,即它们倾向将散乱的素材纳入到连贯、严密的因果情节链中,以引导影像表意。具体而言,当代叙事纪录片大多借用了好莱坞经典叙事“开始 -发展 -结局”三幕式结构,以建立一条或多条最终趋向闭合的叙事弧线,将一系列事件整合到“问题 /解决”的框架中,影像和叙事的暧昧性和多义性因此大大降低。

《推销员》
以获得 202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我的章鱼老师(My Octopus Teacher,2020)为例,这部典型角色驱动型(character-driven)纪录片包含两条紧密交织、彼此映射的叙事线索:一是遭遇中年危机的克雷格·福斯特回归自然、与章鱼相遇并成为朋友的过程;二是章鱼遭到鲨鱼围攻、恢复、成长、生育后代和走向死亡。后一叙事透过福斯特主观视角的采访回忆交代,因此包含在前一条叙事线内部。内外叙事线都采用了角色驱动的三幕式结构,并依照时间逻辑,角色的一系列遭遇与行动构成起承转合的叙事,因果关系体现在人物成长变化的连续性脉络上。最终困境得到解决,人物获得成长,形成了典型的成长叙事。影片剪辑也主要服务于推动叙事而非表达观点或者制造争论,使用了诸多剧情片常见的剪辑技法。如章鱼第二次遭遇鲨鱼追捕的段落采用了连续剪辑技巧,以追逐的叙事逻辑,将不同机位与景别的画面串联在一起,凸显画面中主体的快速运动与空间的不断变化,以强化冲突,拉长悬念,营造紧张激烈的氛围。

《我的章鱼老师》
(三)依靠人物证言来“讲述”故事
当代叙事纪录片的另一特征是依靠人物证言(testimony)“讲述”故事。这些证言大多以采访、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可被看作是解说式纪录片中旁白的变体,其功用是将不同时空的真实素材缝合在一起,并对其进行阐释。不同的是,传统解说模式采用无声源的第三人称画外音,即上帝之声,具有客观、中立、超脱的印象与权威之感;当代叙事纪录片则多以个性化的人物声音作为解说。无论是影片人物的采访或画外音,还是创作者的自述,都属于主观视角下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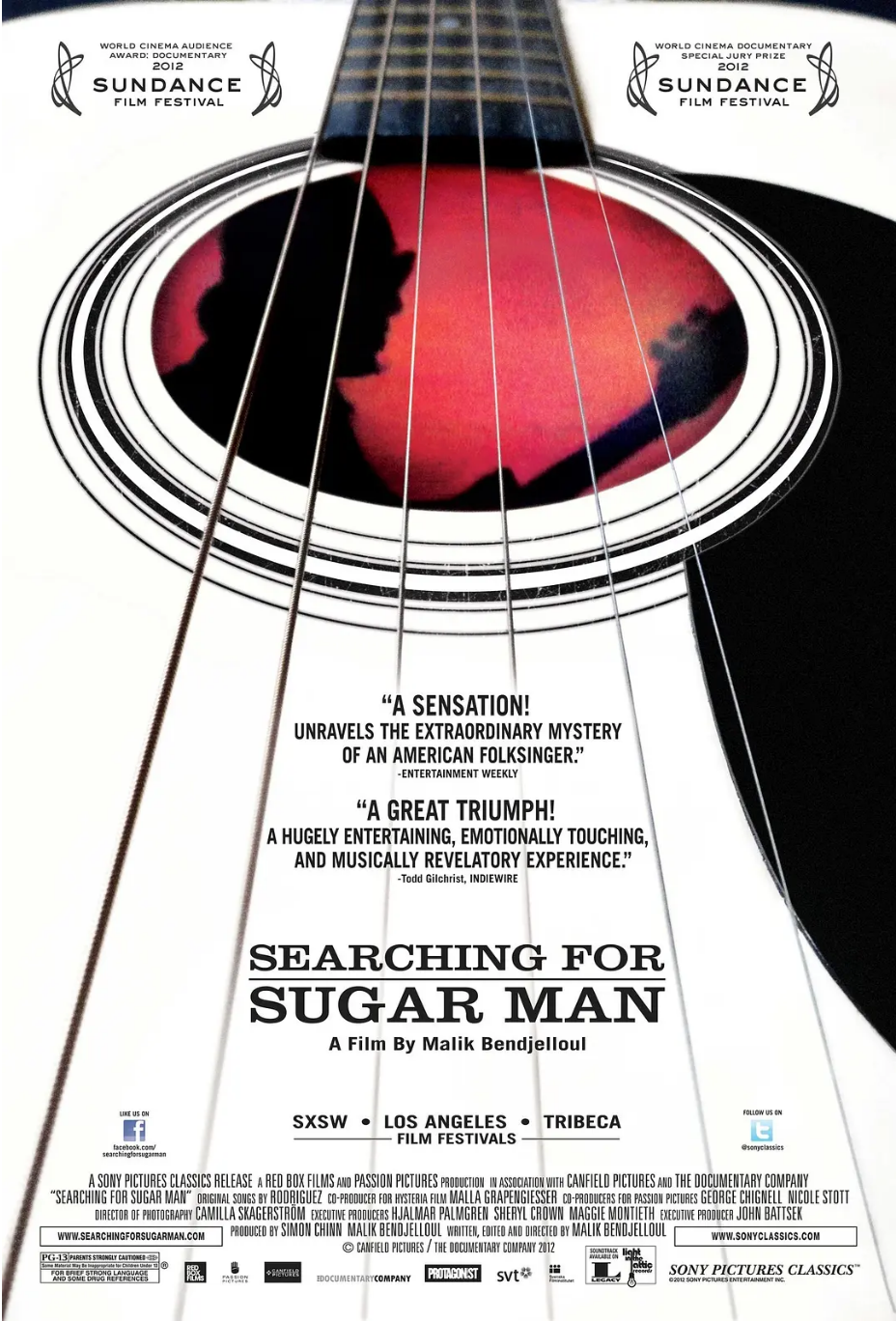
《寻找小糖人》
传统纪录片理论多认为解说破坏了影像的优先地位,引导观众以特定角度来理解画面,因此解说往往被认为有说教意味和操纵影像之嫌,而遭到批评。但纪录片学者斯特拉·布鲁兹(Stella Bruzzi)认为这种批评过于武断,忽视了以解说为主体的纪录片内部的差异。此外,从功用上来讲,解说不失为一种实用而经济的方式,能有效地交代信息、整合画面与叙事、直接向观众发言、传递观点等。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叙事纪录片对个性化解说的使用既避免了说教之嫌,同时利用了解说在解释画面、交代信息与观点等功能上的优势。这种主观视角的叙述直接向观众发言,也更具可信度和亲密感。获得 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徒手攀岩》中,主角亚历克斯的自述承担了重要的叙事任务,以第一人称视角将其童年经历、如何开始攀岩、对这一极限运动的看法、挑战酋长岩的准备过程一一道来。围绕事件展开的《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2012)、《伊卡洛斯》(Icarus,2017)、《泰国洞穴救援》则都采用了多人物证言,事件亲历者被精心挑选,其访谈证词或是对事件的复述,或是对自身经历的回顾,或是对特定人物或事件的评价。这些被精准截取的证词,像是构成整体叙事的一块块拼图,互为补充,并将现场拍摄的观察式影像、新闻报道、社交媒体资料等缝合到一起,形成连贯的因果情节链。
以具体人物的证词代替“上帝之声”解说,也体现了发生在纪录片领域的一个普遍变化,即放弃对终极真理的主张,“强调个人视野”。个体的主观经验同客观事实一样,被视为真相的一部分,是具体化、情境化的知识形式。这样的理念催生了如自反式纪录片、第一人称纪录片、私影像等新形式,个人经验、记忆成为纪录片的表现对象。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曾总结:“传统意义上,纪录片代表着完整、完成、知识与事实,对这个社会、世界及其运转机制的解释。但最近以来,纪录片已经代表不完整、不确定、回忆与印象、个人世界的图景及其主观建构。”当代叙事纪录片亦可被看作是这一整体转变的一个征候,特别是它们普遍凸显了个体人物的中心位置。
(四)人物占据中心地位,以情感认同传递观念
当代叙事纪录片可被粗略分为围绕特定事件展开的情节驱动型(plot-driven)与围绕特定人物展开的角色驱动型。不过,即便是情节驱动型,也要依靠事件中具体人物的经历构成叙事。《泰国洞穴救援》聚焦于引发国际关注的足球少年洞穴被困事件以及相关救援行动,是一部典型的情节驱动型纪录片。但影片叙事依然要透过与救援行动相关的各色人物(如被困者家长、救援领导者、英国洞穴潜水专家、海豹队队员等)展开。这些人物,因其在救援行动中所承担的角色,被精心选择,并按照救援行动的时间因果逻辑组织在一起。在当代叙事纪录片中,人物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

《泰国洞穴救援》
精彩生动、富有人格魅力的人物往往被视为纪录片得以成功的关键。比如获得 2019年圣丹斯电影节观众奖的《登堂入会》(Knock Down the House,2019)被网飞以一千万美元的破纪录价格收购,其成功就被归结为选对了人物。该片聚焦美国地方议员竞选中劳工阶层女性崛起这一现象,以四名出身背景和经历各异的人物勾勒出劳工女性竞选人的群像。不过,影片大半篇幅都给了其中一名人物——竞选纽约第十四区议员的亚利桑德娅。拉美裔的亚利桑德娅不仅年轻貌美,且头脑聪明、充满活力,极具个人魅力。同时,在与其竞选对手——连任十届的白人男性议员——的对照中,亚利桑德娅的人物形象被进一步凸显,也预示了其竞选之路希望渺茫,为叙事制造出极大的悬念,也为结尾奇迹般的转折做了铺垫。

《登堂入会》
当代叙事纪录片也始终在个人故事与更大的社会问题之间创造关联,以实现“以小见大”的效果:个人故事被放置于首要位置,而影片指涉的社会问题、制作者的观点多停留在背景处,透过个体人物的经历来传达。《登堂入会》直面美国政治权力内部的阶级性别问题,但其核心观点——褒扬劳工阶层女性候选人挑战在位政客的革命性意义——是通过精心挑选的个体人物及其参选经历来表达的。获得 202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以火书写》(Writing With Fire,2021)聚焦由底层种姓女记者经营的全印度唯一的女性媒体。影片透过三名女记者的日常生活、个人遭遇以及她们报道的事件呈现了印度种姓制度与父权体制对女性、底层民众的压迫,彰显了被网络和新媒体赋权的当代印度女性追求公平正义的勇气。换言之,当代叙事纪录片倾向于将观点、意识形态暗藏在叙事中。影片对观众的劝说依赖叙事认同机制,即观众通过认同人物的动机、行动而接纳影片所描述的世界以及潜在的意识形态观点。《登堂入会》特别描绘了亚利桑德娅与去世父亲的关系,调用她的女儿身份来引发观众的认同。在叙事层面,父亲去世构成了亚利桑德娅命运的转折点——不得不负担起家庭重担,进入服务行业;同时也成为她参加竞选的原动力——实现父亲的期望。影片最能引发观众共情的片段当属结尾:赢得竞选的亚利桑德娅坐在国会大厦外,动情地回忆起儿时与父亲参观的情景。透过具有普世性的父女关系,观众在人物身上找到了最佳的情感投射点。

《登堂入会》
如果说传统理论大多将纪录片视为一种与科学、教育与社会责任相关的“严肃话语” (discourse of sobriety),强调其理性、客观的面向,满足观众求知欲,那么在当代叙事纪录片中,个体的主观经验与客观事实同等重要,情绪 /情感(affect)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由于当代叙事纪录片通过调动观众的情感认同来实现说服的目的,情感决定着观者与影片及人物建立何种关系,也从根本上影响着影片观点的接受。《我的章鱼老师》的核心情感是福斯特对章鱼产生的强烈认同与自我投射。这种超越人与动物分界的依恋,进一步透过福斯特的主观视角叙述,成为观众认同影片叙事、接受其宣扬的环保理念的关键。在《徒手攀岩》中,除了惊心动魄的攀岩场景,最具感染力的是主人公亚历克斯对攀岩的极度痴迷以及在攀岩过程中展现出的强大意志与自我超越。这些特质激发了观众的欣赏敬佩之情,进而理解了无保护攀岩这一极度危险的运动的魅力。对情感的强调也意味着原本存在于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正逐渐消融。相较于传统纪录片旨在提出观点、制造争论、教育和说服观众,当代叙事纪录片更倾向提供一场跌宕起伏、情感充沛的叙事体验,而这原本是剧情片的诉求。可以说,当代叙事纪录片体现了纪录片美学范式的一种转变,而要理解这一转变的原因以及其核心——对精彩故事的追求,就要从经济与生产机制层面入手,考察国际纪录片制作、传播机制的变化。

《徒手攀岩》
二、国际纪录片制作、
传播机制与故事的商品化
传统上,欧美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主要依赖公共电视台,受政府公共资金的支持,且承担着一定的传播国家文化、启蒙教育民众的功能。西方纪录片商品化的重要节点出现在 20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向以及“文化工业”“知识经济”等议程的提出,欧美国家大幅削减原来支持公共文化事务的预算,公共电视台要依靠广告收入自负盈亏。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也改变了纪录片的制作形式,电视台开始将纪录片的制作外包给独立制作公司,而电视台主要作为委托制作方、采购方和播出平台。
基于纪录片制作环境的变化,一种新的生产机制应运而生,即提案(pitching)。这一机制最初由加拿大独立制片人方佰德(Pat Ferns)提出,并于加拿大班夫电视节首次试行。在提案会上,独立导演或制作人向决策人(即电视台采购编辑和其他采购商)公开陈述项目方案,之后双方洽谈预售或其他形式的合作。此后,提案形式不仅被广泛介绍、应用于欧洲、北美等地区,更在 21世纪前十年,被引入亚洲如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地,成为各大纪录片节展市场板块的必备活动。而提案模式,作为一种全球形式(global format),对国际纪录片市场的形成、纪录片项目的跨国制作和流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提案不仅连接了本土制作者与国际播出平台(如国际电影节、电视台、流媒体平台),也推助了主流纪录片创作理念(包括对故事形式的偏好)的在地化传播。有学者指出,提案论坛不应被单纯视为媒合(match-making)纪录片制作者与投资者 /购买者的中介平台,更要意识到当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鉴于当代纪录片产业本质上是买家市场,决策人在提案现场对提案项目的公开评论、提问,不仅是在阐述其所代表机构的偏好,更是在集体性地展演着一套对于何为“适销纪录片”(saleable documentary)的规范性定义。根据笔者对广州纪录片大会(2015)、CNEX华人纪录片大会(2015、2016)等提案论坛的田野观察发现,公开问答环节中,决策人的点评多集中在人物、情节与故事上,包括“故事是否精彩”“人物是否有弧光”等,而提问也往往关涉故事的未来走向,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故事可能的结尾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点评和提问都证明人物、故事是决策人最关心的要素也是纪录片获得投资的关键。关于故事潜在走向的追问也体现了决策人对于叙事确定性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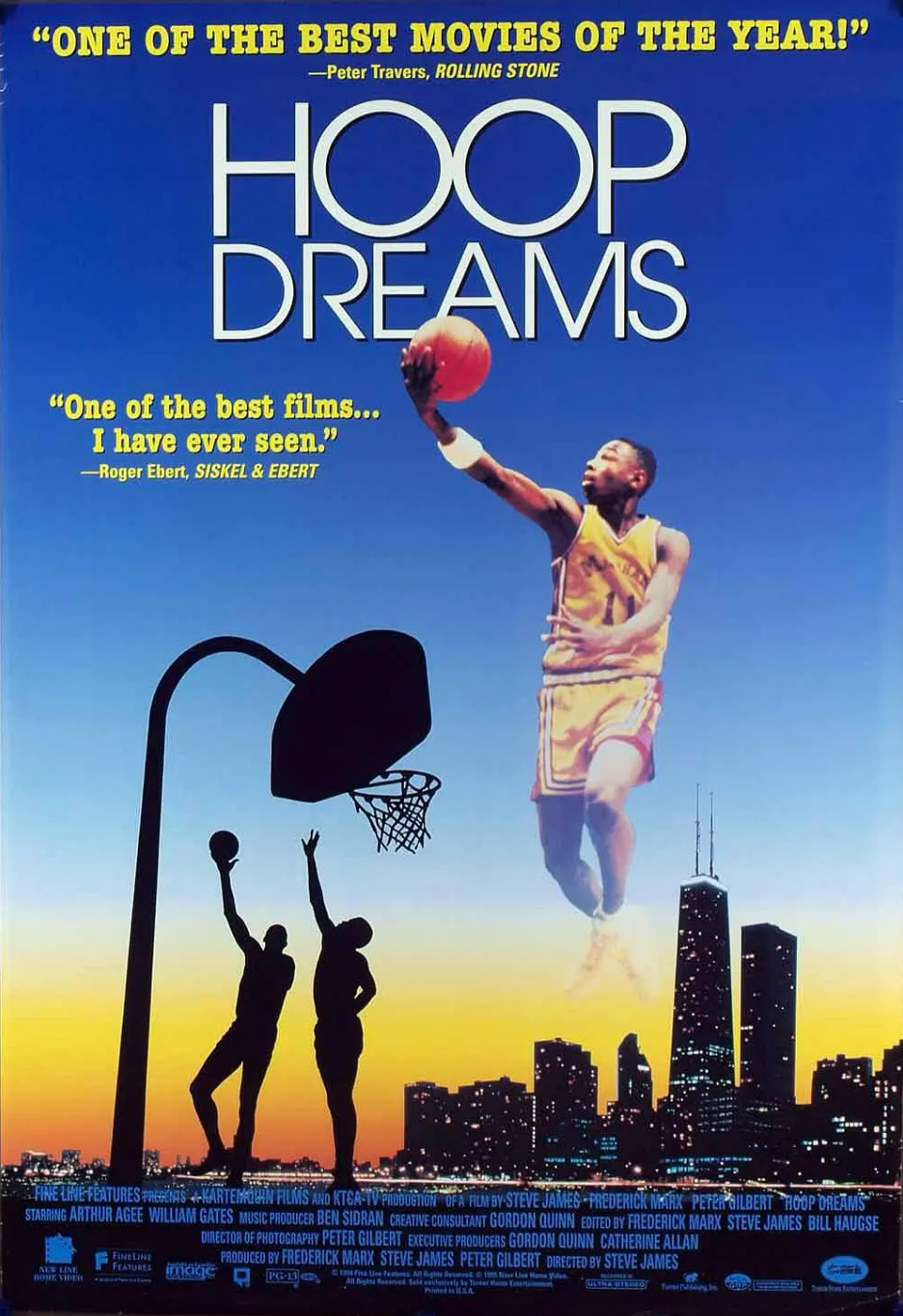
《篮球梦》
在推动纪录片故事化上,另一不可忽视的力量是院线纪录电影的出现与风靡。从 20世纪 80年代末起,纪录片进影院的风潮从美国蔓延全球。《罗杰和我》(Roger & Me,1989)、《篮球梦》(Hoop Dreams,1994)等案例证明了纪录电影也有可能获得高票房并盈利。到 2000年初期,一系列高票房院线纪录电影如《拼字比赛》(Spellbound, 2002)、《冰封168小时》(Touching the Void,2003)、《山村犹有读书声》(ToBe and to Have,2003)、《华氏 9/11》(Fahrenheit9/11,2004)、《寻找小糖人(2012)、《徒手攀岩》(2018)等相继出现,其共同特征就是对角色、故事等叙事元素的使用。这些卖座纪录电影不仅证明了纪录类型的商业潜力,同时也作为行业竞相模仿的标杆,进一步推动了当代主流纪录片的故事化。
针对这一现象,导演、影评人马克·卡曾斯(Mark Cousins)认为,如今纪录片已成为一门巨大的票房生意。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纪录片社会功能角色的变化:原来左翼传统下被用来传递真相与改革社会的纪录片,如今正成为一种新的娱乐消费产品,即纪录片的娱乐商品化。这一趋势从 20世纪 90年代起愈演愈烈。20世纪末开始走俏全球的纪实剧、真人秀节目在吸收了传统纪录元素和手法的基础上,创造出极具娱乐价值的新形式,宣告着 “真实性娱乐”(factual entertainment)时代的来临。随着如网飞、Amazon、Hulu等跨国流媒体平台的兴起并涉足纪录电影与剧集的投资、制作,纪录类型娱乐化浪潮进一步被推向全球。
故事在主流纪录片的主导地位与纪录片娱乐商品化以及支撑纪录片作为商品流通的国际自由市场密不可分。诸多产业报告及从业者都强调好故事是纪录片受欢迎与否的关键。这些产业话语认为,故事作为一种叙事形式,具有超越时间历史的吸引力和跨文化的普世性。然而,这种有关故事的迷思遮蔽了故事形式与当下纪录片制作、发行机制和环境之间的关联,即故事是纪录片娱乐化、商品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事实的故事化处理,纪录片被转化为一种可与剧情片相媲美的视听娱乐商品——在内容上“真实”且引人入胜,在视听形式上尽可能电影化,其目标在于为观众提供一场与“真实”相关的视听体验。正是在纪录片娱乐商品化的过程与结果下,讲故事成为了对事实(actuality)“最好的利用”。故事的“普世性”实际建立在其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上,是故事商品化的体现。此外,这一现象还与新媒体传播环境的“后真相”境况息息相关。
三、“后真相”时代纪录片的故事与情感
英国《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列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意指“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感情和个人信念的情况”。在这一定义中,“后真相”指的是一种状况或语境,而并非某种不同于“真相”的事实建构。在后真相状况下,大众往往被那些“感觉是真的”(something feels true)的事所说服,即便它不一定由客观事实所支持;真相不再(仅仅)诉诸于客观事实,而更依赖于情感和个人信念。换言之,后真相并非声称真理不存在,而是令事实服务于政治观点。正如李·麦金泰尔(Lee McIntyre)指出,后真相相当于一种意识形态至上,其实践者试图让人相信某件事,无论证据是否充足。后真相境况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大众对绝对真相的信仰破产,即大众意识到在政治语境中,事实总是经过挑选,在遮蔽中呈现,以形成对真相的特定阐释。另一方面,后真相的出现与当代媒介信息技术与新媒体网络传播环境密切相关。新媒体的去中介化与即时性导致各种真假混杂、未经筛选的信息直接出现在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碎片争夺着人们的注意力。在信息商品化的背景下和以点击率、算法推送为逻辑的筛选机制下,最终被广泛传播的是那些最吸引眼球、最能触发观者情绪的信息。

《篮球梦》
与此呼应,哲学家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在《虚拟的寓言:运动,情感,感觉》(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中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已经从依靠语言 -符号的规范化管理转向对情感的管理,而后者更强调科学技术对情感流动强度和方向的控制,更关注个体情感如何被引导和被引导至何处。新媒体环境下的各种信息、图像都可以被看作是激发、传递情感的动能之流,权力机制通过控制情感流动的方向和强度来控制和管理人。
回到纪录片领域,在后真相传播境况下,事实、证据、档案等传统新闻和纪录片中最被重视的元素让位于情绪、感觉,以及迎合大众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事实、证据、档案等传统被认为与真相紧密相连的“纪录形式”(documentary form)不再重要。相反,正如视觉艺术家与评论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指出的,记录形式在当代情动经济(affetive economies)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一方面调动着大众对“记录”的传统理解与印象——记录总是与事实、真相有关,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多地通过调用各种影像形式与修辞手段力图作用于观者的感觉与情绪。尽管史特耶尔并没有使用后真相的概念,但她指出的这一现象,无疑与后真相境况以及新媒体传播环境高度相关。从美学层面,纪录形式正是因为符合大众对客观、事实、真相的一般印象,因为被感觉是真的,而在情动经济中被广泛调用。
后真相境况对情绪、情感的重视、利用与当代叙事纪录片通过情感建立认同、传递观点的内在机制不谋而合。比尔·尼科尔斯将纪录片视为修辞艺术,因其不只是传递信息,更旨在赢得赞同;而在争论中修辞比证据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以人物和情感为核心、以建立认同为目标的故事正成为当代叙事纪录片最重要的修辞手段:它们以观察式影像、个性化、主观的人物解说营造出透明、真实的效果,实际上却又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潜在地作用于观者的情感,引发观众对影片叙事及观点的认同。因此,故事的形式不仅仅服务于纪录片的娱乐商品化。部分具有社会和政治议程的纪录片也将“讲故事”(storytelling)作为新媒体注意力竞争环境下调动观众注意力和情感、引发其对特定议题关注,进而推动社会改革的手段与策略。
故事与其核心的认同机制在当代主流纪录片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为纪录片创作带来了一系列潜在影响。通过展现他者的具体处境和经验,唤起观众对拍摄对象的认同,当代叙事纪录片或许有助于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然而,讲故事的方式倾向于诉诸情感而非引发思考,诉诸认同而非保有距离的了解。《我的章鱼老师》将故事核心锁定在主角与章鱼的依恋关系时,影片带给观众更多的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情感体验。这一体验建立在经典三幕式结构(相遇 -相知 -分离)上,并通过对章鱼的拟人化再现以及对福斯特 -章鱼关系的浪漫化处理引发观众的情感认同,但这一策略也大大降低了章鱼及其所处的海洋世界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故事及其核心的认同机制也令创作者倾向于选择那些更讨观众喜爱、更能引发认同的人物,而非更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倾向于展现人物普世性的一面,以引发大众的共情,而回避他者身上异质性的部分以及真实生活的复杂境况。
结语
黑特·史德耶尔认为在全球化影响下,纪录片出现了形式危机;特别是商业纪录片领域出现了“表述的单调”(uniformity of articulation),即作为一种全球化产品,纪录片必须在内容上尽可能独特,在形式上则趋于标准化。当代主流纪录电影的故事化是纪录片形式标准化的一个征候。故事是作为全球商品的纪录片的国际通用范式: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具有本土性与文化特殊性的内容进行处理,将其转化为标准化的文本以实现全球流通,无论其功用是大众娱乐消费或意识形态输出。
近年来,讲故事的方式也在中国纪录电影领域走俏。无论是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作品,如《归途列车》(2009)、《摇摇晃晃的人间》(2016)、《中国梵高》(2016),还是进入院线市场的“真实电影”,如《城市梦》(2019)、《棒!少年》(2020),都采用人物驱动型叙事和经典三幕式结构。与之相伴的,也包括“真实故事”“真实影像”等用于纪录电影宣发的新命名。这些命名一方面意在表明影片具有堪与剧情片媲美的叙事性和戏剧性,同时也强调它们与现实、真实的关联,而后者赋予了影片超越剧情片的特殊感染力与社会伦理意义,召唤着观众的观看行为。“真实故事”“真实影像”这样的命名,既是纪录电影尝试商业化的例证,也是其商业化的策略;故事则被当作吸引大众、触发情感的形式与修辞手段而调用。

《归途列车》
本文在总结国际主流纪录电影故事化转向、探讨这一转向与国际纪录片制作环境和生产机制的变化、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后真相境况之间关联的同时,也意在对故事的主导地位提出批判性的思考。纪录片从诞生开始一直是理解他者、处理差异的重要媒介形式。当纪录电影越来越故事化,越来越倾向于提供一种能够引发观众情感投射的叙事体验时,是否某些原本属于纪录片的珍贵品质和功能正在失去?当讨喜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以及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叙事成为纪录片在电影节和院线市场“成功”的保证时,更多的创作者也会更倾向于寻找讨喜的人物,挖掘他们身上能够引起认同的元素,强调人物(他者)与观众(我们)之间同质性的部分。这样的做法令影片难以真正超越或挑战观众既有的经验与知识框架,也离比尔·尼科尔斯所定义的“严肃话语”越来越远。
图片来源:豆瓣
编辑:李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