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文明的失落与挣扎:为时代力量留影
雨果回到了森林,把城市里的滑板、山地自行车、短视频也带回了森林。Rap连结着雨果在城市里接触到的新鲜事物,和故乡里丢不掉的人生底色,同时,也是年轻的鄂温克人在两种文明之间寻找到的平衡。
年轻的猎人不可能再学会用枪,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传统与现代自洽的生存方式。
本文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阮白卿
柳霞喜欢看太阳。
北方边境,大兴安岭。即使在严冬,太阳依然是耀眼的,无垠的雪地让日光变得更加猛烈,每当这时,已经老去的柳霞都会眯缝起眼睛看着太阳。在鄂温克猎人代代传承的认知里,太阳几乎是一切能量的来源,“足足的,红红的。”
人们可以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窥见鄂温克这个神秘民族的兴衰史。大约300年前,鄂温克人从俄罗斯勒拿河流域雅库特地区出发,穿过西伯利亚的严寒,渡过额尔古纳河,进入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开始了与驯鹿在森林里依存共生的狩猎生活。
鄂温克人与鹿之间的微妙关系,既是猎人和猎物,也是护卫者与馈赠者。对山林生命的尊重嵌刻在鄂温克人代代相传的狩猎准则里:数罟不入洿池,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才有人类的繁衍生息。然而盗猎者的枪破坏了这里的规律,当无节制的贪念侵入森林,鄂温克人传承数百年的生活方式也被摧折了。
当猎人失去了猎枪,民族的勇气是否依然存在?导演顾桃用20年的时间观察这个在时代巨变下失落的边境民族,并将他所看到的一切拍成纪录片《敖鲁古雅》《犴达罕》《雨果的假期》。在影像中,他目睹着鄂温克人的迷茫、探寻和回归,并在无奈里深刻地与之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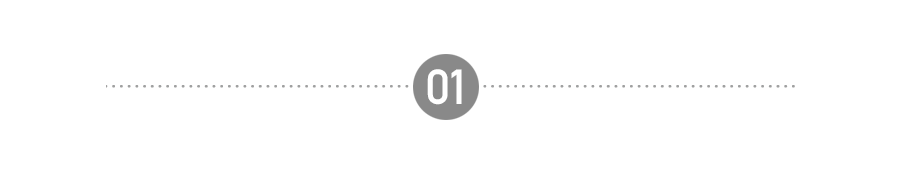
寻找与生活的连接
对鄂温克的最初印象,来自父亲顾德清带回的照片。
相机和胶卷是父子之间为数不多能够交谈的话题。在顾桃才十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拉着他一起洗照片,小平房点着昏暗的红色灯泡,有放大镜,有投影,相纸上出现雪地驯鹿的脚印和骑着驯鹿的鄂温克女人。
这时是20世纪80年代,鄂温克人尚未被收缴猎枪,猎民、狍子、驯鹿、积雪、森林、太阳、月亮……平等地组成了大兴安岭的生态。拍出这些照片的父亲,被这原始的和谐吸引着,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也融进森林。
后来顾桃意识到,父亲是在有意识地让他感受影像的力量。18岁以后,顾桃去哈尔滨学美术,“感觉自己逃离了家庭的束缚”。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做过北漂,搞过设计,做过摄影,却越来越困惑,“漂泊在这么大的城市里,作为个体生活和城市的关系,一直找不到一种连结点。”2002年,顾桃重回内蒙古,恰好那段时间父亲刚刚出版了《猎民生活日记》。
 影像成为顾桃和父亲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
影像成为顾桃和父亲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
彷徨期的顾桃读了那本书,勾起了许多和父亲的回忆。“书里有我和他一起洗的照片,也有我帮他整理的文字——一开始的记录,都是随手拿个烟盒就写了,笔记零零散散。”
那些他亲自参与整理过的影像,带着20年前的神秘气质,深深吸引了顾桃。两年以后,顾桃沿着父亲的路线而行,走进父亲曾经投入全部热情的敖鲁古雅,试图用影像的力量找到与父亲的情感连接。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顾桃的纪录设备跟父亲相比有了大的变化。伴随着DV的普及,顾桃也开始选择用“动态影像”的方式进行记录,在记录中他发现,视频能帮助他更好地捕捉到“自然的喝酒后的流畅感和流动的伤感情绪,很真实”,逐渐找到了“像我自己的那种呼吸”。
 顾桃开始用“动态影像”方式记录北方边境民族。
顾桃开始用“动态影像”方式记录北方边境民族。
遗憾的是,直到父亲去世,顾桃都未找到合适的机会给他看自己的片子,但鄂温克故事传承到了顾桃的人生里,过去交流甚少的两代人,通过镜头里的生活完成了连接。在对同一个民族的影像记录中,顾桃与父亲完成了情感的碰撞和交汇,也终于产生了理解与共鸣。
但顾桃片子里的边境民族,已变成失落的一代——禁猎后的鄂温克沉溺在酒精里。《犴达罕》表现出的,是猎民们挣扎在原有生活的消逝和对现代文明的不适之中,他们喝酒、互殴、感慨、沉默,悼念即将死亡的狩猎文化。在世俗意义上,“一个放下了猎枪的民族,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然而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替鄂温克人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
 最后的使鹿部落鄂温克族人和森林中的驯鹿 图/新华社。
最后的使鹿部落鄂温克族人和森林中的驯鹿 图/新华社。
人们说,顾桃关于鄂温克的影像记录,是狩猎文明最后的挽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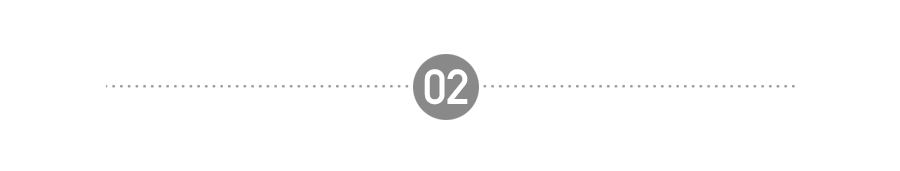
柳霞的太阳
从顾桃的纪录片里,人们记住了诗人维加,还有维加的姐姐柳霞和男孩雨果。
雨果在遥远的无锡读书,像从森林里放出去的风筝,飞得太远,三年才能收回一次引线。2007年拍摄的《雨果的假期》里,镜头记录下这个年轻的鄂温克男孩和母亲的疏离:雨果坐在炉膛前,柳霞一次次喊他,“你过来,我想跟你聊聊天”,雨果始终没有向她走去。母子之间相隔的,不仅是成长历程中缺失的三年时间,更是现代文明和狩猎文明之间巨大的隔阂。柳霞一遍遍地问,大兴安岭好还是无锡好?最终她赌气似的承认,“那是你的世界,我们管不了。”
舅舅维加断言,城里长大的小孩不一样,他们和森林的感情疏远了。柳霞感到失落,但她始终记得,雨果离开大兴安岭时问她,太阳叫什么?她说,叫喜温,那是她给雨果起的名字。雨果说,那你看看太阳吧,看看太阳就能想起来我。有一个片段没有被顾桃剪进片子:柳霞面对阳光舞动双手,将太阳当作雨果,喃喃自语,“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能长翅膀回来看看我?”
太阳指引着猎民的生活,16年后,当柳霞再次面对顾桃的镜头,她仍然维持着上一代猎民的日常状态。她对着3点钟就要落山的太阳说,“太阳是有时间的,天上的星星(太阳)就是鄂温克人的钟表。”这令顾桃感受到鄂温克人对狩猎文明的怀念,于是这支新的片子被命名为《柳霞的太阳》。一如他在前三部片子中所做的那样——按下拍摄键,一切真实的生活,无论喜怒哀乐,尽数收入取景框。
顾桃专注于对真实生活的捕捉。片子中,当他进入房间后,把那部用了几年的华为手机直接立在高架子上,他则像这家的另一个“儿子”一样和柳霞自然地互动交流。只留手机作为他的“眼睛”,捕捉、记录着生活的每个真实瞬间。这部用华为手机拍摄的生动真实的《柳霞的太阳》,最终荣获了第四届华为影像·金鸡手机电影计划“最佳纪录影片”荣誉。
 柳霞望着天上的太阳。
柳霞望着天上的太阳。
过去的16年让柳霞在雪原上的行动更加迟缓,却也让雨果这个当年怎么都骑不上驯鹿的男孩和森林越来越近。雨果在城市里度过了他的青春期,他一度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告别了驯鹿和母亲,“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孩子。”为此他打过许多工:做保安、超市搬货、后厨洗碗……他爱上说唱,为了这个梦想,又去到成都。南南北北,雨果生活了好几个城市,但似乎在哪里都没有真正地融入。在《柳霞的太阳》中,柳霞等待的太阳回到了她身边——雨果决定回到大兴安岭的猎民点,回到母亲身边生活,“带着一身的疲惫,也带着一份坚守。”顾桃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自白。
“城市很好,但那不是我待的地儿。我是属于森林的,我的家人、我的驯鹿都在森林里。”
镜头外的顾桃开始明白,自己之所以深深为鄂温克人着迷,不仅因为日渐衰落的狩猎文明,也因为他和雨果一样,在写一个关于逃离和回归的故事。
“雨果在各种城市游荡,反而和故乡产生了连接。在城市打工,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也没什么尊严,反倒是在森林里又有了尊重。我18岁时离开家庭,走出小镇,现在想想,和他们其实是一样的。”顾桃谈起最近一次原本和雨果约定的见面,在成都。雨果下了山,听说驯鹿营地来了三头狼,因为担心母亲和驯鹿,又匆忙赶回山里,“他和森林的关系,还是很紧密。”顾桃把雨果的变化留在他的影像里,从《雨果的假期》到《柳霞的太阳》,情感在两代人之间流动,成长亦有了具象的对比。
 在城市中长大的雨果又回到了森林。
在城市中长大的雨果又回到了森林。
顾桃想起,自己在人生的彷徨期回到家乡,重新拾起父亲的影像记录工作。逃离故乡,又找回和故乡的情感连结,或许是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注定要遇到的共同的人生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他自己就是雨果。
顾桃在影像中走进了雨果的生活,也在影像中共情雨果。他鼓励雨果也拍点什么,“拍你妈妈的太阳,你的驯鹿,你的森林,用手机就行。”其实记录并没有那么难,他所拍摄的鄂温克故事,固然是民族文明的宏大叙事,却也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在《柳霞的太阳》的结尾,顾桃把很长的一个镜头留给雨果,让他在山林里唱了一段Rap,那是他自己创作的歌词,其中有他作为狩猎民族的后代所面临的现状,有对古老智慧的怀念,也有他的成长。“我想把它作为一种纪念,让人们都看到雨果的成长,所以一定要保留下来。”顾桃说。
Rap连结着雨果在城市里接触到的新鲜事物,和故乡里丢不掉的人生底色,同时,也是年轻的鄂温克人在两种文明之间寻找到的平衡。雨果回到了森林,把城市里的滑板、山地自行车、短视频也带回了森林,这在上一代是不可能的事。有了这些,年轻一代才能在森林里“待得住”——除了看护妈妈,看护驯鹿,还有这些娱乐方式能够与他们为伴。年轻的猎人不可能再学会用枪,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传统与现代自洽的生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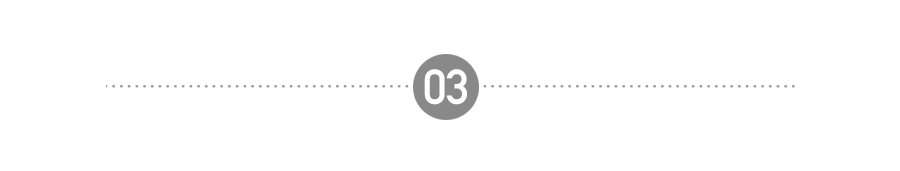
为时代力量留影
顾桃一直在追逐正在消失的文明。
2011年,顾桃的另一部纪录片《神翳》上映,片子的主人公是鄂伦春族唯一健在的萨满关扣尼,镜头如实留下了另一个边境民族即将消亡的信仰。
八年之后,关扣尼逝世,顾桃受邀拍摄了萨满的树葬。萨满的离开让他意识到,被时间带走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人去记录,它们就真的死亡了。从这时候起,他踏上寻找不同民族的萨满的旅途,记录他们祈福、占卜、治愈的仪式。顾桃把这一路的探寻称为“萨满地图”。
记录下来是否就能够对抗文化的消亡?在边地拍摄了20年,顾桃并不认为有什么能抵挡时代的洪流,面对鄂温克的迷茫,他“只能感受到无奈的现实”。但记录可以让文化在影像中得到永久的留存。顾桃说,“影像是留给未来的档案。”就像父亲虽然已经过世18年,但直到现在,依然有学者在研究80年代的北方民族时,以顾德清的文字和照片为基础。有个陌生的年轻人找到顾桃,送给他一篇长达10万字的论文,都是在看了他们父子关于鄂温克的记录后做出的研究,并且现在也在从事民族文化方面的工作。顾桃觉得,这才是影像的力量,“在时间流逝之后,也可以感受到当时情感的流动”,不是在当下,而是在未来。
顾桃曾做过摄影师,在“读图时代”,也试图用图片去讲故事,最终他发现单张的图片很难做好个体的表达。动态的影像“能够更自由地记录到声音、活动和人的情绪”。维加的诗、柳霞的孤独、雨果的成长,整个鄂温克族隐藏在时代背后的声音,都在影像里得到了表达。这是父亲用照片难以定格的流动的情感。影像技术的创新发展给了记录者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
从鄂温克三部曲开始,顾桃的拍摄器材一直在变化,最初是DV,也用过单反,后来变成了手机。在华为手机拍摄出的《柳霞的太阳》中,穿插了《雨果的假期》的片段,画面对比强烈。带有明显年代感的影像提醒着观众,时代一直在前进,这个家庭已经走过了16年的时间。
 《柳霞的太阳》中加入的十年前的记录片断。
《柳霞的太阳》中加入的十年前的记录片断。
这并不是顾桃第一次用手机拍纪录片,在捕捉生活记录当下的诉求上,DV很难支撑他的需求,“得从包里拿出来、摘镜头盖、开机,还得调一下曝光参数”,等一切准备就绪,事情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像他那台华为手机的便捷和准确,“一个取景器,上下左右”。
《柳霞的太阳》开头,极具东北特色的动物狍子从画面中穿过。“开着车,看到两个跳跃奔跑的狍子,很快地就能拿出手机抓拍下来。如果用DV,再找三脚架,我拍不到这么有灵性的动物。”顾桃说。
哪怕在纪录片导演的眼里,器材也并不是最重要的。顾桃的作品带着不加修饰的粗砺感,这正是他要的效果,他记录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真实发生的生活。“你用手机拍摄,手机就是你的眼睛、你的精神。”他觉得这是一个“自说自话”的时代,没人能够制定标准来评判影像创作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追寻你自己的呼吸”——顾桃把对真实生活的感知称为呼吸——“你是如何感受这个世界的?文字也好,影像也好,音乐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
生活从来都是最好的剧情,手机的易操作性,让呼吸的频率更容易被追寻到。20年左右,顾桃在草原上用手机记录日常,“我每天早上起来拿起手机就跑着去追马”,在快速运动中,手机仍可保持画面平衡,这种轻便、随意的记录,成为了当时的他生活的出口。后来“我在稍微大的电视或者是投影上看,画质上没有差别”。手机影像技术的进步,让每个人、每时每刻记录生活的“质感”更高。
 手机成为记录真实生活的一手取景框。
手机成为记录真实生活的一手取景框。
华为影像·金鸡手机电影计划连续4年如期举办,鼓励每个普通人举起手机,捕捉生活中转瞬即逝的情感和片段,形成独属于手机电影的风格和文化。移动影像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创新,也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拿起手机记录或表达生活。从硬件配置到软件算法,从影像技术到影像文化,华为手机在影像领域长期深耕,为专业摄影师及大众均提供了更多创作手段,满足了更多创作场景,带来了更为丰富全面的创作内容及题材,这是对工业电影尤为重要的补充。
时代的进步带给人们更大的思考空间,移动影像的发展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可能。在一段段鲜活的影像中,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生活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时代的力量。正如在影像中找到了“北方呼吸”的顾桃所说,设备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哪怕只是一部手机,“横着拍就是电影”,重要的是,一直记录“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