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色”时代的两部黑白获奖影片—《罗马》与《冷战》
201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的得主是《罗马》的摄影师兼导演阿方索.卡隆,同年,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ASC)却把年度最佳摄影颁给了《冷战》的摄影师卢卡斯.扎尔。
如果说以演员为主体构成的奥斯卡评审委员会的选择更多的代表了观众口味,那么ASC这个由全世界最顶级的电影摄影师会员们的投票则代表了专业观点。令人惊奇的是,有一点他们的选择是一致的,就是同时选择把奖项颁给了一部黑白影片。
电影诞生一百多年来,色彩已经成为摄影造型中最核心的元素之一,在2019年,两部黑白片却同时获得奥斯卡和ASC大奖,这引发了我的好奇和思考:到底是黑白影像本身不朽的魅力还是这两部影片对黑白影像的使用有了创新性的发展,或者是当代观众和创作者同时开始怀旧了?


在多次反复对这两部影片进行拉片观看后,我又查阅了一些幕后制作的资料和主创们的访谈,对他们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有了一些了解,发觉把这两部片子放到一起看,去比较它们,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种比较让我有了很多兴奋的发现和领悟。
黑白是电影一开始的样子,今天很多人喜欢黑白色调则可能是因为黑白对于世界有一种视觉和精神的高度提纯。这两部影片都采用了黑白色调,但创作者的动机则显然是不一样的。
《罗马》的导演兼摄影指导卡隆阐述说:“我想要拍数字黑白电影,想用现代电影镜头来回顾过去的时光。我会避免那种带着长阴影和高对比度的经典、风格化的画面,而是走更自然的黑白画面风格。我不想要为了追求所谓的‘电影感’而隐藏数字科技,而是更从容地探索数字科技所呈现的画面。每种媒体——胶片和数码——都有其语言和其优缺点,但我想要探索数字形式下其令人惊艳的动态范围”,他在在色彩方面,利用数字摄影机巨大的动态范围,对一些画面的色彩去饱和,从而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忧郁般的自然主义’黑白影调,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点对比度,则将其描述为‘柔和的自然主义’。
而《冷战》的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则说,他一开始是想把影片拍成彩色的,因为他的上一部影片《修女艾达》使用的是黑白摄影,他不想重复自己。但是,他后来发现,影片所要表现的那个年代的波兰历史是灰暗的,自己找不到更合适的色彩去表现,所以无奈之下还是选择了用黑白影像来呈现。


虽然都同样选择了黑白,但出发点不一样,意图不一样,这种迥异的观念就决定了他们在技术细节上的个性化差异表达。
阿方索·卡隆在决定选择黑白影调后,他花了6个月时间做前期的筹备工作。他和卢贝兹基拍摄《地心引力》时,大部分使用的是Arri的AlexaClassic。在经过对胶片和数字摄影机做了大量测试后,最终锁定了配备改良单色传感器的阿莱ALexa XT B+W这台设备,或者使用阿莱Alexa 65拍摄彩色影片,然后通过在后期降低饱和度的方式拍摄。
据说卡隆一开始对大画幅是持怀疑态度,但卢贝兹基最终说服他使用Alexa 65。导演后来也承认,在做技术拍摄做测试时,他意识到这部电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尊重,片中的角色需要一个更大的调度范围,他要拍大广角,并且平衡前景和后景,他的观念是人物是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这样的导演意图,决定了在画幅比、光学镜头和景别的选择,《罗马》选择了2.40:1,更多的选择了广角镜头,人物特写很少,大多是全景和中景。
而《冷战》则选择了1.33:1,摄影指导卢卡斯.扎尔说之前拍摄《修女艾达》使用这个比例给他了一个很好的启示,这个格式能打造不太过于明显的构图。他觉得在宽画幅中,摄影师经常会无意识地将人物优先放置在画面中的黄金分割点上,这种方式强调意图过于明显,但1.33:1这个画幅比则为演员和环境之间提供了一种平衡。他很多时间选择将摄影机放在高处俯拍,他强调自己为了打造深度而不是广度,就像立方体,它里面有许多层次的盒子,摄影师将摄影机放在这‘盒子’外面,利用其深度,向里面拍摄。


在构图方面,《冷战》很强调画面的象征性,比如我发现一个演唱会场景中,斯大林巨幅画像在舞台后从一个人物近景局部升起,然后跳到一个大全景,这种象征性的两极镜头的运用给我了极大地震撼,让我很直接的理解了此时主人公的感受,理解了他接下来要坚决离开波兰的行为动机,这个镜头让我想起了《烈日灼人》里田野上巨型气球带起斯大林画像的镜头。但主人公在社会公共环境里时,作为个体的他总是和人群保持着距离,与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个人与社会主流群体和价值观的这种疏离和隔阂,使观众能够比较透彻的感受人物内心的那种孤独和忧伤。
人物在空间环境中时,也更多的选择让环境占据大面积的构图,把人物放到画面的最下方,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和压迫感,当人物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时,观众最终得到的是一种隐喻的、象征性的、广阔的空间。





卢卡斯.扎尔说,诸如广角镜头、中景和特写,当使用这些常规镜头时,通常会显得平面。他从《公民凯恩》堪称景深教科书式的范例中得到了启发,于是他大多数场景里都选用了F5.6或F8,试图将一切都构建在深度中,尽可能打造更多层次感。
令人惊奇的是卡隆在拍摄《罗马》时也基本采用了小的光孔,意图得到更大的景深,当然他的这种选择有一部分是面临技术限制时迫不得已的妥协。拍摄《罗马》时选择的镜头是阿莱Prime 65,卡隆认为效果很好,但他在测试时很快就发现,使用大画幅镜头带来的不足之处是,要将光圈调到T4.5-T5.6之间才能得到他想要的影像品质和风格。如果大于这个光孔值,影像就会变得柔和并有点断裂,边缘会非常的明显。当开拍后,据说卡隆惊讶地发现用T5.6光圈需要的光量太大了。他觉得自己像在50年代拍电影,一台巨大的摄影机和大量光线!而且卡隆不想要那种长且一成不变的光轴,他想获得是那种自然的柔和光源,但他的拍摄范围很广,从房子的一个角落就能看到屋内延伸的一切内景。这需要大量反射光、漫射光透过窗户,才能在室内获得足够的曝光,于是他们几乎调用了整个墨西哥所有的18K灯。
在照明和光线上,《冷战》的摄影指导则说,前期筹备时,他看了许多老电影,像《卡萨布兰卡》、让-吕克·戈达尔和其他法国新浪潮导演的电影,以及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和米洛斯·福曼,他还看了很多照片,比如玛丽莲·梦露和波兰明星Kalina Jędrusik,研究过HelmutNewton的摄影,发现他使用了很多美化光,能够在摄影中打造惊人的对比度,除了摄影本身,还体现在美术设计上,墙壁、脸部、服装、头发和化妆等等。于是,当自己决定使用大景深时,就很清楚要通过照明、服装和美术设计将人物和背景进行分开,他说他是在拍摄《修女艾达》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拍《修女艾达》时他使用了大量侧光和背光。因为《冷战》中有许多场音乐会,就必须使用和《修女艾达》不同的灯光,此外,导演希望灯光设计让人有60年代感,所以自己就使用那个年代给女演员打光的照明方式。


在氛围和透视营造方面,《罗马》更多的选择了用丰富的道具和场景,并没有过多的依赖于气氛的雕刻。卡隆避免使用除ND外的镜头滤镜。他说对于室内景和大空间,他决定不用烟雾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法能营造出美丽柔和的背景,但他拒绝使用这类工具,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因为他想打造锐利而无颗粒感的画面。
但《冷战》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大量的在室内放烟,尤其是在巴黎的戏份,视野局限到很狭窄,美术设计甚至都开始开始取笑摄影师,说巴黎这是影片中最贵的地方,可我们却看不见巴黎。也许景深真的太浅了,但摄影指导说他需要为此而战。因为他想打造这种视线仅落在某些人上面的感觉,即使在巴黎,他也希望影片的视点只落在这两个人身上。于是,Wiktor和Zula在巴黎的相遇相处时,从未展示广角镜头或信息镜头。但在柏林时,每个镜头都是和Wiktor有关,围绕他建立了一个世界。


在运动和调度设计方面,《罗马》采用了单镜头方式,为电影提供始终如一的视角,让人能忽略镜头,卡隆将之描述为“客观的”,通常是放在Dolly轨道车上,有时是搭配稳定云台或遥控头。没有一个手持式或斯坦尼康镜头,导演表示:“使用这些工具会改变镜头语言。”偶尔使用起重机,也像Dolly轨道车一样,但它没有推拉的动作,只有摇镜头和跟拍镜头。对于运动,影像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几乎全部是固定跟摇和轨道横向跟移,找不到一个纵向推拉移动镜头,这种克制代表了一种视点,导演和摄影师有意让观众成为一种客观的观察者,而不是深入其中的人。即使在一些紧张激烈的场面中,摄影师也没有使用惯常的手持晃动,而依然是一种稳定的客观视角,比如女主人公分娩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戏,摄影机就是在脚架上,定定的,一个长镜头让我们看到了始终。期间,焦点始终在女演员身上,后景焦外忙碌的医生们是虚的,那一刻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女主人公的无奈、无助和痛彻心扉的悲伤。
而《冷战》的摄影指导却说,在运镜方面,一开始不要太经常移动摄影机。当它移动时,它不会与人物或动作同步,摄影机只是在描述这个世界,慢慢揭露这个世界,他希望这种讲述看起来是自然而不刻意的。之后,随着故事更趋向为叙述式的。当Zula出现,摄影机就跟随她。她是触发器,是摄影机动的契机和能量。当演员变得情绪化时,摄影机也变得更情绪化,比如当她歌唱时,用手持摄影机来表现。在巴黎的场景,摄影机完全和Zula及Wiktor同步,始终跟随者他们。由音乐舞蹈驱动,这意味着有大量的运动。之后,完全进入叙事,充满人物,这就是所谓的巴黎。当Wiktor和Zula在一起时,就用斯坦尼康或轨道车跟随他们。
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这两部电影在开篇镜头的处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一个摇的长镜头,《罗马》从俯拍地面和地面的水倒影摇起,再到跟摇人物的活动;《冷战》从俯拍一只演奏乐器的手摇起到乐手的脸,再摇摄到其他乐手的脸。长镜头仍然是文艺片的显著标签,导演和摄影师仍然偏爱于用一个长镜头开场的方式来告诉观众,你接下来即将欣赏的是一部文艺片。另外一个相似是,这两部片子的开场镜头和结尾镜头都选择了呼应,《罗马》开篇镜头是俯拍地上水倒影出天上的飞机,而片尾则是仰拍天空,天空飞过一架飞机,这两个镜头几乎是彼此互为镜像,无论经历再多的磨难,生活人在继续,太阳照常升起;《冷战》开场戏是男女主人公相遇相识的地方,经历的相爱相杀的男女主人公在片尾再次回到了他们一开始相遇的地方,选择了在这个地方一起结束的生命,人生如梦,似乎一切都如没有发生,一切都没有意义。
如果对于电影来说,所有的影像都是剧作和导演创作意识的外化,那这种闭环式的结构则不仅是剧作的机构,也是视觉的回溯与照应,对此,卢卡斯.扎尔说,他认为一个地方总会有最好的一个角度能揭示你讲故事所需要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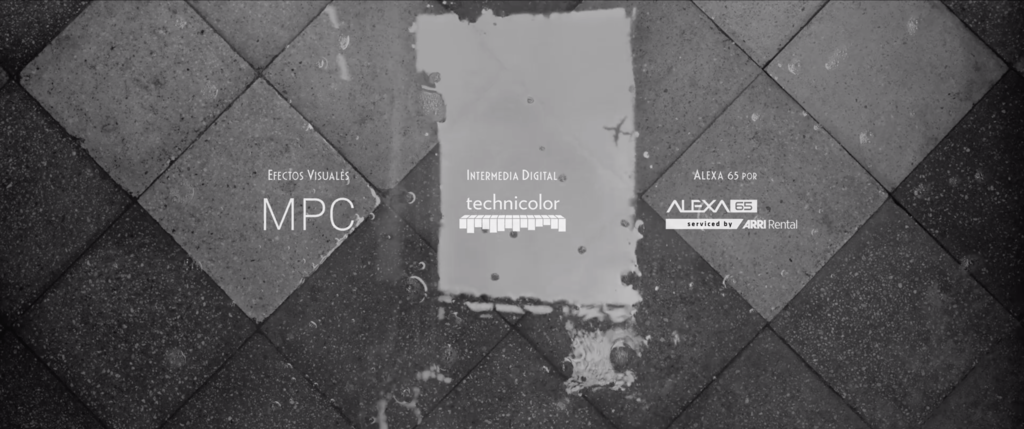

此外,在两部片子在剪辑时对影像序列的处理方式也很有各自的特点,《罗马》中有很多全景接全景的处理,在《冷战》则大量的使用了从特写直接跳到大全景的这种两极镜头,同时,《冷战》对静态镜头进行了大量的使用,静态镜头和动态镜头的衔接方式也很有创意,影片用了很多黑屏转场,用字幕的形式提示着年份和地点,以此来作为故事的节点。
这种方式可能会为观众带来一种不舒适的观影体验,而这种适当的不适感则极大地帮助了观众对主题和人物的理解,时间跨越干净利落,黑屏制造出留白,这些故意的时间空白,让观众丧失了很多信息量,但这种不适感恰与两个人物人生中互相成为空白的感受相辅相成。


同样是黑白片,但两部电影在影调和风格追求上,甚至是严重相左的,《冷战》很有经典黑色电影的味道,在画面中有大面积纯净的黑,有明显的黑白灰分布处理,而《罗马》则竭力避免这种经典黑白电影所具有的影像特征,甚至是在有意地去颠覆经典和背叛传统。对于经典的继承发展和背叛,都可能是一种伟大的创新,这是拉这两部片子给我最大的收获和体会!